2010年,42岁的山东菏泽农民朱之文,骑着自行车去参加选秀。上台前,他花光所有钱,买了一件二手军大衣,裹在身上。唱完歌,“大衣哥”就火了。
后来,朱之文去了《星光大道》,上了春晚,成了草根明星的代表。一同出道的还有旭日阳刚和阿宝,后两者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惟有大衣哥,和他所在的朱楼村,依然能生猛地撞入我们的眼帘。
“大衣哥”朱之文已经整整五天没有出现在朱楼村了,这是一个坏消息。对村民而言,这是一个比麦子染了病虫害更可怕的事件。
一个早起喂鸡的村民隔着自家低矮的破泥墙,目睹了几个河南人,开着两辆黑色商务车,把朱之文接走了。他迫不及待地将这个独家信源告诉给每一个遇见的人,并从对方或惊讶或失落的反应中,获得某种满足。
没人知道朱之文什么时候回来。传得最揪心的一种说法是,朱之文最快也要五一节之后,才会回家。

无数人的计划被打乱。那些打着“朱之文某某邻居”、“朱之文某某亲属”拍摄短视频的年轻人首当其冲。他们本打算借着小长假,再捞一波流量,可主角儿不见了,无米下锅了,有人开始抱怨,“走了不打招呼,不像话。”
天南海北慕名而来的人们,也扑了空,许多人不甘心,守在大铁门前,从早等到晚。朱家斜对门的干瘪老头子朱于发,身上蓝色中山装泛黄且打满补丁,他背着一篓干掉的洋葱皮,一面跟来访者絮叨,“老三每次去北京演出,最多一星期,去县城买东西,去远一点的商丘,都是一天就回,他离不开村子的”,一面跟人推销自家的客房,“十块二十块,你看着给,我吃啥,你就吃啥。”
突然,一个中年男子对着紧闭的朱家铁门引吭高歌,唱不到两句,隔壁邻居推门而出,朝人群吼:“唱什么唱,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块匾,上书“大衣哥演出接待室”几个字,最底下留着一串业务电话,但他从未接到过一个商演电话,绝大部分打进电话的人,问得如出一辙,“大衣哥在家吗?”
“不在,不在,不在……”连续说了五天,他有些慌了。
没有大衣哥的朱楼村72岁的牛敬文是朱之文的粉丝,两天前,这个老人骑上一辆30年历史的永久牌自行车,从山东兖州的家里出发,骑行10个小时,跨越300多公里,成功摸到了朱之文的家门。他没有导航软件,路上全凭一张嘴问,从市里问到县,从县里问到镇,到了镇口,问朱之文的家在哪,围上来一堆人给他指方向。
牛敬文当过村书记,后来在司法系统下岗,打回农民,由此郁郁寡欢。他希望通过写作证明自己,多年攒下了200篇诗歌,歌颂英雄人物,赞美风土人情,送到县里的报社,人家以庙太小为由,婉拒了他。
他想到了朱之文,幻想着朱之文能够在北京的舞台上,把自己的诗歌唱出来,他事先想好了说服朱之文的话术,“你只会翻唱别人的歌曲,你唱了我的歌,就是原创”,他还专门为朱之文写了一首歌,将其与黄河、梁山好汉并列放在歌词中。

没见到朱之文,牛敬文很失落。他眯起一个眼,通过铁门上唯一一个小洞,朝朱家院里使劲瞄。64岁的潘圆紧挨着铁门,坐在角落里,她从河南商丘赶来,随身携带一个巨大的编织袋和一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演出道具,一套玫红色带黑边的旗袍穿戴整齐,一旦朱之文露面,她随时随地都能表演,获得肯定后,再说明来意——通过朱之文介绍认识韩红,以期寻求韩红基金会的帮助。
朱楼村至今穷困,本村人很少有能买得起小轿车的,条件稍好的,多是买电动小三轮或者小四轮,所以但凡是开车进来的,几乎都是外来人。车牌也是五花八门,江西、四川、海南、陕西、河南、山西、江苏、浙江,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还有穿洁白的衬衣、笔挺的西裤,带了司机,开着奥迪来合影的粉丝。
但是和朱之文在村里时比起来,如今这点人气,几乎可以忽略。济南的两个自媒体人将单反对着朱家大门架起来,“在网上看到,来这里的人特别多,我们就想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他们很失望,蹲守了一天,便撤了。
小卖部老板娘朱玲娟巴不得天天人挤人,她的店面距朱之文家不到20米,正好位于朱家和停车场之间,进村的人们停好车往回走,都得路过她的店,以前她不敢进饮料,村里没人消费得起,一瓶营养快线在货架上能放到过期,现在她的冰柜里不仅有可乐雪碧,还进了不少冰淇淋,付款码挂在门上,自取自付,方便得很。
在朱楼村,对外来人抱有欢迎态度的人,可能只剩下朱玲娟了。但她最近开始不安,如果朱之文一直不回家,冰柜里的几箱冰淇淋就可能卖不出去,她就得一直让冰柜开着,她有点舍不得了,也开始抱怨,大衣哥不在,为啥人就不来了?
警觉的村庄朱楼村的人坚信,朱之文生在朱楼村,长在朱楼村,是朱楼村让朱之文出的名。所以,朱之文回馈乡里,是应该的,但外人想要跟他们分一杯羹,却并不那么受欢迎。
蒋生(化名)现在可能是最不受朱楼村欢迎的人,因为他刚刚抢了村里人的好处。
两周前,朱之文的家门被两个粉丝一脚踹开,视频很快就在网上疯传,最先发出的视频,就出自蒋生之手。“他拍那一脚,就赚了四千块钱。”村里人在传这句话时,语气并不好,言下之意,朱之文难道不是朱楼村的专属吗?这钱,只能是朱楼村的人赚。
很快,针对蒋生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流言就出现了,他被描述成“在外省混不下去的一个不良少年”,有人干脆给他扣帽子,说他已经换了三个媳妇儿。
他没跟当地人说起过自己的来历,他觉得没这个必要,也是不屑,打心底看不起他们。去年初,他来到朱楼村,租下一个房子,开起传媒公司,追拍朱之文的日常。除了做直播,他很少出现在镜头前。在这个村里,除了房东和朱之文一家,他几乎不跟其他人来往。
他的脑子确实更活络,也更敬业。朱之文不在,村里的年轻拍手们,也不见了踪影,他们最擅长、也是唯一会做的,就是将手机怼到朱之文的脸上,或者炮制出各种大衣哥的亲属,但朱之文不在,他们也懒得出门。
蒋生不一样,拍朱之文是他的事业,他需要随时准备大衣哥的外出,他用直播来填补这块空白。他在一旁听说牛敬文骑了10个小时自行车,就像狼嗅到了肥肉一般,一把将老人拉到镜头前,一边添油加醋地讲老头子的惊人举动,一边让他唱歌,唱朱之文的成名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牛敬文唱了两句,从包里掏出一打稿纸,开始换话题,他说自己写了钟南山的诗,想说说院士的大爱无疆,蒋生立刻打断了他,“粉丝只想看大衣哥,你说其他人都白搭。”牛敬文不听,还要继续说,蒋生果断将镜头挪开了,临了还调侃道:“老爷子不懂直播,大衣哥的粉丝,就是那么土。”
“他们不喜欢我,因为我靠脑子、靠本事,光明正大地赚钱,他们只会蹭大衣哥。”蒋生说,他能理解朱楼村人对外人的敌意,“他们都能看到网上的批评声音,家丑只能自家人说,外人知道了,他们首先对外人产生敌意。”

下午三点左右,朱善阔穿一件紫色polo衫,远远地推着自行车过来。这个时间点,是朱楼村路上本地人最多的时候,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开着电动三轮车,从角落里钻出来,通过朱之文捐助的唯一一条水泥路,聚到村南新建的长廊下聊天。
朱善阔却不一样,他慢悠悠地晃到朱之文的家门口,站在离人群不近不远的地方,冷冷地打量这些外来人。偶尔有认识他的人,会上去跟他握个手,寒暄两句,他也不给好脸。旁人提醒,他是朱之文的亲侄子,还是朱之文的经纪人,在村民眼里,他的身份似乎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我走上前主动攀谈,问他是朱之文的侄子吗?他斜着眼,从头到脚将我扫了几眼,从他眼神中,我感觉出不耐烦,他冷冷地回答,我不是。我继续追问,你是朱之文的经纪人吗?这次他扭开脸去,干脆没看我,用当地的方言回答,我不是。我不甘心,继续问他有没有做短视频,粉丝有多少,他一口否决,“我不做那个东西。”
很快,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他的妻子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光屁股小女孩,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站到他跟前,举着手机,竟然开始拍视频:“这是朱善阔的房子,后面就是大衣哥的园子,风水宝地,想租房子的打上面的电话,欢迎联系朱善阔。”
朱善阔脸色一沉,主动跟我搭话:“我们只是随手拍一下,我们不做电商,也不卖东西,我们不会靠大衣哥赚钱。”听上去,他在为之前的否认辩解。
他撒谎了。有同村人路过,随口问起他,上次和朱之文出门演出,感觉怎么样,“就那样吧。”他急切地应付过去,转身离我远了几步,然后蹲在他那间待出租的房子跟前,不再说话。
那是一个用废弃集装箱改建的出租房,他花了7000块钱从县城运到村里,简单地装修,租金4000块钱一年,感兴趣的人不少,有一个浙江商人跟他谈过价,想打个折,他不肯,他相信有大把的人想要跟大衣哥当邻居。

事实上,当大衣哥的邻居会时刻面临外人的盘问,在来访的粉丝眼中,全村人都欠了朱之文的钱。“我们没跟朱之文借过钱,可能以前有人确实两万三万的借过一些,但一两年就还了,不还钱的,都是他的亲戚,都是一家人嘛,借钱不还也正常。”朱于发老人说。
“咦,朱之文的话,你们哪能全信,他从小聪明着嘞。”
聪明的朱之文朱于发睡完午觉,习惯跟六七个本村的老头子,凑在一起闲聊,以前是在村中央的一块杨树林底下,如今村南口的小公园建起来了,他们就去那边的长廊下。建这个公园,朱之文捐了一些钱,“他带个头,不全是他的钱。”
公园路对面,就是朱之文曾经练习唱歌的杨树林,边上的小河干涸见底,再远处的麦田已经改建成了大片太阳能电站,这个能源公司能进村,也是朱之文从中牵的线。
朱于发说,朱之文只有小学文化,但很聪明。家里三兄弟,他排最末,农忙时,别人都去干农活,他跑到林子里去大声瞎喊瞎唱,时间久了,村里人就说,朱家出了一个神经病,家里人也不敢再强求他干农活,索性就由着他。
慢慢的,朱之文的唱歌水平高了,村里一旦来个外人,他就跑去给人唱歌,人家就说这是个人才,“我要是不种地,每天唱,肯定也不孬。”

“你说他现在回来种地图什么?他哪里还用种地,这不就是做给你们看嘛,那天粉丝都追到他地里去了,他就在那里给人唱歌,哪能叫种地。”
踹门事件更加应证了他们嘴里对于朱之文的设定。门被踹开之后,朱之文并没有发怒,而是出门和守在门外的粉丝合影,跟他们一起拍视频,这被村里人认为是朱之文聪明的地方,连蒋生都认同“这波操作很神,赔了一把门锁,换来全网热搜,这两天记者都来了好几拨了。”
但他似乎对此论断并不笃信。
朱之文家有三道门,最外一道大铁门,进去一个水泥小院,然后是被踹坏的那道木门,再进去才是长着大槐树,种满花草,挂着灯笼和风车的园子,穿过充满野趣的园子,才是他的两层小楼。
踹门之后,朱之文装了两个监控,一个放在最外那道大铁门上方,正对着门口,一个装在小楼外侧的墙上,正好能监视到一侧的围墙和中间那道木门。他还在围墙上竖起十根铁栏杆,装上了铁丝网,原本不过两米高的矮墙,一下子变成了三米多,围得严严实实,从外面看,倒像是一座监狱。
以往,偷偷地翻墙入院,是拍客们最喜欢的视频素材,一则朱之文冷着脸将不速之客送出门外的视频,被打上“粉丝被大衣哥撵出门”的梗之后,随随便便就能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获得几百万的播放量。墙升高了,断了人财路不说,朱之文也少了一条曝光的路径,因此蒋生才想不通朱的做法,“但他又很乐意打开门,主动配合陌生人的拍摄要求。”
“想不通,真想不通,他好像心里很矛盾。”蒋生说。
出不了村,入不了城“哎呀我去,房地产广告都打到这里来了”一个从四川眉山专程赶来的粉丝,趴在铁门的缝隙里,朝里张望。
他应该看到了第二道门左手边那根灯杆上,挂着的三幅地产广告了。朱之文在家时,最外头的大铁门通常是打开的,人们挤在木门前,那里成了天然的演播室,当地村名和粉丝们可不讲究,能拍到大衣哥就行,至于背景出现什么广告,他们懒得管。
于是,聪明的商人们开始打起主意来。小院儿头顶挂满了菏泽邮政的大红灯笼,上面印着广告语“存款到邮政”,两棵槐树下挂着本地装修公司的广告,地产公司的易拉宝支在角落,太阳能路灯上的广告纸似乎是有意没撕的,汽车抵押贷款的小横幅挂满了巷子口,连垃圾箱上也打上了不知名的某个品牌名称,公安部门似乎也不想放弃扩大宣传的机会,防诈骗和禁毒的宣传材料,赫然贴在朱家大门上。
唯一跟朱之文有点关系的,是门上的一张书法作品,天籁之音,年前一个山西的粉丝送给他的,如今被撕了一半,只剩下天籁两字。
牛敬文懂点风水,等朱之文不得,便煞有介事的分析起他这座院子的风水。说来也怪,整个朱楼村方方正正,屋子大多坐北朝南,大门都是东西方向开,唯独朱之文家的门楼,是朝东南的,“歪的嘛,哪有朝东南开的门,说明这家人不正。”
“他的房子在死胡同里面,并且路往前不通头,前面是河挡着了,我们讲究背山面水观阳,他这个不是个发财的风水。”牛敬文分析地头头是道,末了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分析的人,正是自己的偶像,赶紧把话给圆了回来,“但他运好。”
一个济南人跑来租下了朱之文家斜对面的一个小房,在面朝马路的一面开了门窗,挂起了几块牌匾,“小本创业优选平台”,“美容瘦身养生产品”,“工厂直供产品”。开门不到一个月,隔两天,他都能刷到在大衣哥出没的不同视频中,出现过自己的门面。后来他意识到,加盟电话放在牌匾最底下,容易被人群遮挡,第二天他就动手将电话挂到了门檐上方,很快,“每天就能接到十几个咨询电话。”
他的房租一个月不到500块钱,他坦言,自己来朱楼村,并不是做生意,就是占一面墙打广告。

朱之文为什么不离开朱楼村?
喜好唱歌的潘圆有自己的理解,她看来,最能展现朱之文唱功的歌曲,并不是他的成名曲《滚滚长江东逝水》,而是《好汉歌》,理由是梁山好汉的故事,发生地点在运城,身为本地人的朱之文,对宋江等人、对家乡的理解,超过了刘欢,他能把这个当地的味儿唱出来。如果朱之文离开了农村,去了北京,跟刘欢比哪还有优势?
90后的蒋生说得更直接,“他得保持持续曝光啊,除了出门商演,他哪有其他机会营销自己,年轻人追星会去机场电视台堵偶像,找朱之文,大家都知道来朱楼村。”
朱之文应该是国内最容易找到的明星了。
“你看看围在他家门口的这些粉丝,都是农民,朱之文能进城去吗?进不了城,他在北京买了房,就是不敢去住,离了农村,他就不火了,必须是农民身份,才能火,哪怕是去二十公里外的单县,他都不能火。”
从河边唱歌的杨树林,到装扮一新的自家花园,朱之文将村子当成了自己的舞台,他会给村民、访客喂素材,他有热度,村民粉丝扮演了流量的分发者,他再靠接商演变现,其他人则通过短视频赚到钱,在蒋生看来,“这是一对互利的关系,他出不了村,也入不了城,现状对他是最优解,不矛盾。”
如果这一点被证实,朱之文的确是聪明的。
他讲了一组对比的案例。两周前,朱之文在村里时,村里人山人海,车子堵得动弹不得,停车场上挤满了卖货的小摊贩,急得当地派出所赶来撵人,生怕出什么岔子。但这几天朱之文外出后,人流就大幅下降了,虽然他在河南商丘被路人拍到,正在逛古玩市场,但外出的流量与在家相比,“差了不是一丁半点。”
难怪朱于发老人逢人就说,“他离不开村子的”,村民需要朱之文,朱之文也不能没有朱楼村。



 朗读本文
朗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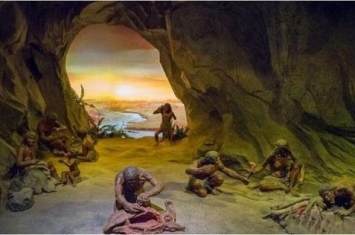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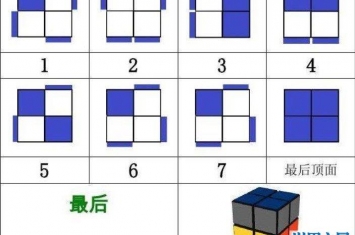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