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高的女性。”

1938年8月,潘多出生在藏兵营一间马厩里。
潘多刚长到8岁,父亲病故了。
孤女寡母无法生活,只得沿村乞讨。
她们从江达县乞讨到日喀则,一路上忍饥挨饿,受尽了人间的屈辱。

潘多直到现在,仍然忘不了农奴主放出狼狗撕咬她的可怕的情景。
那是一个严寒的隆冬,她和母亲来到一个村舍。
她让母亲坐在墙根避风,自己去敲一户农奴主的大门。

她一边敲门,一边乞求:“行行好,给一口糌粑吧!”
门开了从院里窜出一只凶恶的大狼狗,扑到潘多身上又撕又咬。
潘多睁大了惊恐的眼睛,一边呼救一边逃跑。
腿上被咬烂了,鲜血流淌着,一滴一滴洒落在洁白的雪地上……从此,见了深宅大院她就害怕得全身发抖,离远远的就躲开它。
潘多12岁那年,她母亲终于病倒了。

从此,小潘多每天从早到晚坐到织氆氇的机子跟前,干她妈妈干的活。
她个子矮小,坐在凳子上,双手还够不着机子。但她把坐凳垫高,吃力地织呀织。不织,她们就会活活饿死!
第二年,潘多刚满13岁,就成了一个奴隶。
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妈妈,走了3天8夜的路程,到一个山谷里去给领主放牧牛羊。
成群的奶牛养肥了,她却饿得更瘦了。
一年365天,她天天过着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
她想妈妈,从早晨起来,一直想到晚上。深夜里,更想得慌,常常泣不成声。
领主听到哭声,凶神恶煞似地骂她:“三更半夜哭什么,你这个不吉利的女妖魔!我的家都给你哭倒霉了!”

说着,揪住潘多的头发乱摇乱晃。
她被折磨得实在无法待下去了,她想逃跑。但她的双脚流着血,疼得钻心。
和她一起受苦受难的奴隶们同情这个小姐妹,偷偷地用烧热的羊油替她烫脚,止住了血,止住了疼。
她终于逃跑了!她逃出了虎口,跑了8天8夜,回到了自己妈妈的身边。
母亲看到小女儿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伤心透了。
母女俩抱头痛哭了一场。

母亲对女儿说:“再不能让你一个小女孩去受这样的罪了。苦,我们娘俩苦在一起,死,我们娘俩也要死在一块儿。”
上哪儿去找活路呢?当时商人正在招收背伕。
母女俩走投无路,开始了当背伕的苦难生涯。
然而,商人只不过是贵族、领主的另一个名称而已,母女俩刚出虎口,又进了狼嘴。
她们跟一帮穷人一道,一路乞讨到锡金;然后从锡金背东西回西藏。
喜马拉雅南麓是亚热带气候,常常大雨滂沱;而北麓,又常常雪花飘飞。

还有的山,下面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山顶却是冰天雪地。
在这样的地方行走,往往一夜之间就要经历迥然不同的两个季节。
但无论在南麓还是北麓,她们都只穿着那么一身破衣服。
鞋底子磨烂了,脚底板被冰雪冻得发紫发黑,龟裂的大口子渗着鲜血,钻心地病痛。
这支背伕队伍,有年迈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年轻的妇女,也像有潘多那样的小孩。
有的老人身后还跟着七、八岁的娃娃。
这支队伍里,也有不背东西的家伙,他们手里拿根鞭子,专门监视、打骂背伕。

有一次,翻过了一座雪山,背上的木箱压得潘多实在受不住了,她走到一块岩石边,想放下箱子,休息一会再走。
谁知一不小心,木箱碰裂了。
商人的监工跑过来,破口大骂:“XXX,工钱不给了!还要赔偿损失!”
一边骂,一边举起鞭子就往潘多头上抽打。
潘多的母亲猛扑上去,用自己的身子保护女儿。
她的目光,愤怒地瞪着商人监工。

这时,周围的背伕们蜂拥过来,七嘴八舌地说:“不要说木头,石头也会碰碎呀!”
有的大声喊道:“不许打小孩!”
在大伙的保护下,潘多才躲过了一顿皮鞭的抽打。
一路上,不断有人倒下去。有的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有一天,一位30来岁的年青妇女,昏倒在山路上。
她发高烧,浑身打哆嗦,无法跟着队伍往前走了。大伙把她安置在路边的一个岩洞里。
潘多和母亲还走过去,看望了这个穷苦的姐妹,在她身边留下了一点糌粑。

等她们下次又路过这里时,这个可怜的年青妇女还躺在岩洞里,但早已浑身僵硬。
在世界屋脊崎岖的山路上,她们也不知亲眼看见过多少冻死、饿死的穷人。
也许是这个缘故,那时,潘多对那些银装素裹的山峰,不但没有爱,而且充满着恨。
1958年,跟潘多相依为命的妈妈去世了,潘多孤单一人在人世间。

幸运的是,那时的西藏高原,终于来了解放军。
潘多被分配到拉萨的“七·一”农场,成为了西藏的第一代农业工人。
她住的是砖瓦房,盖的是新棉被,穿上了花衣衫。她仿佛变了一个模样儿,显得那么强壮有力,显得那么活泼有神。

面对着这一切,她的耳畔老回响着母亲临死时对她说的几句话:“毛主席才是我们穷人的贴心人,是大救星啊!”
正是这些特殊的生活经历使潘多懂得,当一个人从生活的最底层走出来之后,应该怎么去生活、王作。
“我去!”“我去!”一群藏族姑娘围着一位穿军大衣的瘦瘦的汉族同志,争先恐后地嚷着。

潘多也挤进人群,对穿军大衣的那位汉族同志说:“我报名……”。
后来,她才知道,那位穿军大衣的瘦瘦的汉族是著名的登山家许竞。
他是来西藏招收登山队员的。
登山是怎么回事,她也弄不明白。
当时她想,可能是给解放军带路。带路,她倒真是个人才,当过背伕,熟悉许多山路……

一位身穿大白褂的医生把潘多叫到屋里检查了身体,又叫她做了做俯卧撑。
一星期之后,许竞坐着吉普车到农场,把潘多、西绕等7个女孩子拉走了。
“拉我们去哪里?”潘多好奇地问。
“去新疆登慕士塔格峰!”许竞告诉她。
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被称为“冰山之父”。

潘多和西绕头一次登山就征服了这座山峰,打破了法国女子克·郭刚保持的7456米的世界登高纪录。
1961年,她又跟队伍们一道登攀海拔7595米高的公格尔久别峰。
虽然她和她的好友西绕又一次创造了新的世界登高纪录,但下山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那天天气特别怪,骤然间烟云从四周的山谷汹涌而上。

暴风雪刮得昏天黑地,把天空遮盖得严严实实的,大白天竟似漆黑的夜晚一样,站在对面都看不见人影。
她和西绕从山顶往下才走了几米,天就黑得再也无法往下走了。
这一夜,她们就睡在山顶下的一片雪地上。
没有帐篷,钻进鸭绒睡袋,拉上锁链,就入睡了。
冷呀,也许冷得发木了,也许困倦得忘乎一切了,她们居然都进入了梦乡,一觉睡醒,拉开锁链,睁眼一望,天像水洗过似的,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明亮耀眼,是一个晶莹辉煌的世界。

前一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鸭绒被堆积着厚厚一层白雪。
坐起身,往四周一看,差点把她们吓昏过去。
多危险呀,她们竟是睡在悬崖的边缘上。
从她们睡的地方,再往前去一米,就是万丈深渊。
天虽然万里无云,但大雪把这座山峰的一切都覆盖得严严实实的,把一切冰裂缝、陡崖……都掩藏起来了。
她们的脚上,到处是险情。
在下一个雪坡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潘多就像腾云驾雾似的向山下滚去。

仿佛是雪崩塌,冰雪把她吞没了。
她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白色的死神——雪崩了!真是九死一生,她居然没有死。
当她感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睁眼一看,雪崩把她打出100多米远,又是在一堵悬崖边上停住了。
她的大半身子埋在深雪里,只露出一个脑袋;气都喘不过来了。
高山眼镜、冰镐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口气。
她赶紧挣扎出双手,扒开周围的积雪,小心翼翼地离开悬崖。

糟糕,双眼怎么疼得直流眼泪呀?得了雪盲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她虎口逃生,总算脱险了。
可她的好友西绕再也找不见了,白色死神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
潘多难过地大哭了一场。她面对着雪山,久久地站立着,站立着,深深地哀悼她的朝夕相处的姐妹。
“潘多,下次我们去登珠穆朗玛峰,我们一定要征服这世界最高峰!”这是西绕在公格尔久别峰顶上对她讲的话。
想不到,这几句话竟成了她的遗愿。
潘多一直牢记着西绕的话,梦想着有朝一日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她知道,每座山峰都有无数的险情等待着她,都有白色死神等待着她,但她不畏缩。

她已经变成一个爱跟高山雪峰打交道的探险家了。
她等待着等待着,一直等到36岁那年,才等到一个喜讯:中国登山队将再次组织攀登珠穆朗玛峰!
这时潘多住在无锡婆家。
她已经是生了三个孩子的妈妈。最小的女儿才生下半年……还能登山吗?
年轻时,她健壮得像一头牦牛,摔起跤来,连许多小伙子都不是她的对手。

可如今,她已经跨入中年人的行列,而且变得这么胖……
潘多的心激烈跳荡着,夜里也睡不安宁。她拍打着6个月的小女儿,嘴里不停地说:“小乖乖;妈妈又要去登山了!”
她的心谁也拴不住,早已飞向西藏高原,飞向珠峰脚下的绒布寺……

1975年5月27日下午两点半,潘多和她的8位战友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大平措、贡格巴桑、次仁多吉、桑珠、阿布钦历尽艰险,终于踏上了地球之巅。
在仅一米多宽的珠峰顶部冰雪之上,潘多静静地躺了六七分钟。
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登上珠峰的女性,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
她和战友们最终用自己的英雄业绩,又在世界登山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五星红旗在峰顶迎风飘动,潘多站在红旗下,那么自豪!
一个从生活的最底层走向世界最高处的女性,能不激动,能不自豪吗?
她是应该自豪的。中国妇女,不,全国人民,都为她感到自豪,她的英雄业绩,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心。

进入90年代以后,潘多已经是一位50多岁的妇女了。虽然,她不能再去登山,不能再去饮冰卧雪了。但她仍然在为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而竭尽努力。

她从西藏高原来到江南水乡,与丈夫和三个孩子在无锡落了户。
她担任了无锡市体委副主任,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但她仍然是一位普通的登山队员,在新的事业的山峰上,奋勇向上登攀。

1998年,潘多退休。
2008年7月16日,赶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70岁高龄的潘多亲自带领30多位志愿者,重新登上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一号营地,祭拜队友,同时为奥运加油。

2014年3月31日,潘多在无锡病逝,享年75岁,自此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



 朗读本文
朗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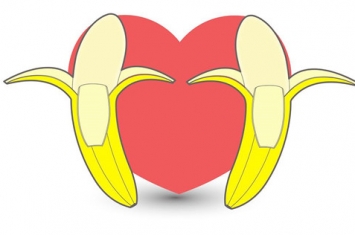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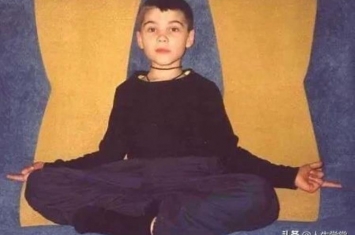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