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故事开始之前,先谈谈名字的问题。名在我故乡是极有趣的一件事,有时间从村中走一遭,听一听,梳理梳理,就会发现其中的奇妙之处。
比如男的按照五行取名,就有了木生、金生、石生、火生、水生、火古、水古、林古、金古、石古、火宝、石宝、土宝、金宝、水宝、树发、石发、金发、水发、根发,按月份:正生、贰生、山生、红生(红就是四的本地读音)、五生、六生、七生、发生、九生、满生,如是种种。
女性也有走五行的:金秀、火秀、石秀、林秀、水秀,金凤、水凤、石风、林凤;按月份的有:正秀、贰秀、山秀、红秀、五秀、六秀、七秀、发秀、九秀、满秀、头秀,外加福秀、玉秀,一直秀到底。此外,就是叫化仔叫化妮、贱古贱女、胜古胜女,成龙成凤,过房仔过房女,山倌倌女、黄冈成金、玉莲玉兰等等。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到来,又出现了以地方来取名字的:广东、福建、湖南、河南、西安、南京、北京、成都、南昌、赣州、福州、广州、三明、宁都、兴国、新安、九江等等,只要是顺口切能和姓氏进行略作搭配的,便能成为高频率的常用名。
总之,有个原则,不要太贵气,最好是贱一点,最好跟路边捡来的一样没人疼,和别人家的孩子一般嫌弃,神不喜欢,鬼不惦记,无灾无难,长命百岁。若是太金贵的名字,被鬼神惦记,而自己又福薄命浅,兜不住纳不了,则反而要产生极大的坏处,甚至一生的命运都要影响。类似的案例不少,但最典型发生最高的,就是如三宝这样的名字。
三宝三宝,佛法僧三宝,天上地下人间的至宝,看着很普通,实际是了不起的大的很,老一辈取名字缺乏想象力,抓破脑袋,脱口而出就是它了,所以,一个村里四五个乃至十几个三宝,实在是常事。
可说来也奇怪,几十年来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什么样的人配什么样的名,取名伟古的,一般都是矮矮胖胖。叫根金的,性格都比较执拗。名为头秀的往往相对较为泼辣。当然,其中最为出名还是取名为“三宝”的一群人,因为这个名字之下,深究起来往往都是些奇离古怪的人物,再看看其生人生经历和生活现状,会不得不惊异,魔咒似乎真的存在。
笔者分析了二十个自己熟悉的三宝,发现三宝们不管年纪大小,姓什么?住哪里?竟似乎但凡粘上了这名字,就要么脑子笨不好用,要么妻离子散成个老光棍,要么成了神神道道精神不正常,要么下狱吃牢饭,要么孤家寡人流浪乞讨。所以,流传一句话,当你想骂人笨蛋时,就会说“你就像是三宝样哩”。

这里要讲的这个三宝,大抵情况和前面所说的类似,也是一个我们村里神奇的人物。还记得第一次听到他的故事是在大约五岁。某天村里大孩子对我们说“诶,你们这伙小孩子,知道不,我们村里有个人会腾云驾雾呢”,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腾云驾雾,于是就问他“啥叫腾云驾雾啊?”。
他说“河对面的三宝啊,前几天我放牛的时候遇到她,说自己有法术,想去哪里的时候就从天上弄一片云下来,自己坐上去,然后喊一声驾!驾!驾!眨眼的功夫,那云就会带他去他想去的地方,这就叫腾云驾雾”。初始我颇觉神异,
其后,又因常和三宝的一个侄儿玩耍。他大我三岁,收我做跟班,他指东我向东,指西我向西,一切都听他的。但这大哥却是个最会吹牛皮的小子,常擅于绘声绘色的说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兼之其父又是某个单位的领导,生活富裕,走过不少地方,所以,也不管真假,我便一揽子全部相信了。
于是我问他“你二伯是不是会腾云驾雾?”,结果他自然是告诉我层亲眼看见三宝从天上扯一片云下来,念几声急急如律令,那云彩就会带着人走。而且作为其小侄子的特别待遇,还跟着一起坐过这个筋斗云,上过村里最高的帽岭峰,去过广东福建等等。他真真切切的描绘了一通,将道听途说与电视电影收音机的东西,尽皆好似亲临般,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全部打通了,一股脑子的讲了出来。
也亏得他讲故事的天赋这般卓绝,听得我目瞪口呆,顿时对三宝崇拜无比,简直立马就要膜拜成了无所不能的神仙,更是生出的找机会拜师学习仙法道术,以逍遥世界的想法。

崇拜一两年,只因我住半山腰,而三宝家在河对面,河两岸的孩子又拉帮结派,经常厮打,使得我七岁上小学时才第一次见到真人。不过,也只是见他个子不高,黝黑油腻,胡须拉茬,头发乱杂,老旧垢满中山装,破烂回力塑胶鞋,左手拿竹梢,右手执牛绳,腰间绑柴刀,表情严肃,一声不吭,每日早晚,走田过坎,寻荒草地,进老深山,就干一件放牛的事。似乎无甚么仙风道骨,神秘高人的样子。
这头母牛是他唯一的财产,支持着他三四亩梯田的耕种,日日相伴,就像是老朋友。但是对待老朋友,他却并不温柔,相反,粗暴的令人震惊。牛婆稍微不愿走,他便用棍子或竹子抽得去。而牛的背上就经常是起了一条一条的痕迹,虽然常话说水浸的牛皮八尺厚,也的确是经不起他的孽待,所以很多人一看见他打牛就会说他是造恶造孽,活该光棍死了老婆。
是的,三宝其实是有过老婆的,还给他生过儿子,可是据说在四十多年前就忽然母子一块病死了,从此他就和他的牛以及老母亲,窝在大集体时分到的两间土房子里,单身叮当的过着。
死了老婆那么多年,他不是没想去找婆娘,哪怕只是半夜里的也好,可事实上,他是个典型的矮矬穷,个子不到一米六,皮肤黝黑,胡须拉茬,常年穿的深色徒步中山装的衣服,身上总是带着汗收馊和牛粪的味道。
哪怕村里那些夜里最是开放好客的婆娘,一旦看到他的样子都不会愿意靠近三尺,何况半夜开门。人说老光棍的家什三把火,于是就有人三宝的玩笑,讲他耐不住时,竟然会找自己的牛婆来解决问题。乡村的事情最容易开也最不能开荤的玩笑,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传的仿佛确有其事,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后面的一切想象和论证都自动生成,到最后谁也不知道真假了。
于是,便有人莫名的传出,说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看见他站在上一丘田的田坎,让牛婆站在下一丘田,他掀起了牛婆的尾巴,直接在牛婆身上解决。事情一传,举村哗然,三宝瞬间从无人问津的边缘,变成了话题的核心。
无人辨其真假,亦无心追求真假,只是多了奇闻怪谈,于茶余饭后,不亦乐乎。不过,身在舆论旋涡的中心,三宝却越来越隐没在这个村庄。天还没亮他就开火做饭,然后带着饭盒赶着牛去了山里,日落黄昏,看不清人时,他驮着一大把柴火,避开了许多人,经过河边曲曲折折的田坎,一声不吭的回家。
后来别人问他弟弟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他弟弟这人很缺德,什么没风没影的事情也会形容的绘声绘色,他说自己是见过,见了之后还回家叫老婆打了一碗汤来祛晦气呢。这件事情在村里传了几年,传到三宝耳朵里,让三宝几年都抬不起头来做人,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玩笑取乐,不知道他是什么感受,当然大概也没多少人在意他的感受。

不管什么感受吧,笑也好,谣言也好,他都没具体回应和争辩,只是默默的忍受,像个木头人,或许也像个修行人。是的,从某种意义上,三宝算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修行人,他没剃度,没进道教或佛教的系统中,家中也从不供奉神佛,但却是常年茹素,不沾荤腥。
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吃斋的,因为很少人和他一起 吃过饭,很少人会具体关注他的 饮食。大概能揣测的,应该是从他的妻儿去世之后,就剩下这条老光棍,便渐渐地成了斋公了,不过这似乎也应合他三宝的名字。
二十多年来,在和老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他的确似乎是没有砍过肉吃,也从来不见他到山上打了什么野味,兄弟家过年请他去吃饭,他也以自己吃斋为名,推脱不去,去了顶多吃点青菜豆腐,草草了事。
他的那些邻居也有人说看见他偷过别人的鸡,证据时早上小河边多了一堆鸡毛。也有人说他到街上时,会去小店里吃肉饺子或者清汤混沌,或是砍了肉半夜里偷偷煮了,再要不然野外放牛,把肉装口袋里,架起柴火烤了。
总之,人们也似乎不大相信斋公一事,在不相信的情况下,便多了许多想象和揣摩的空间,故事也便生长而出。不管有没有真实发生,其实只要冒出了一个小尖尖头,立马就可以化茧成蝶,蝴蝶煽动翅膀,左邻右舍的茶余饭后,自然多了些闲谈笑料。

三宝总是沉默的,被人调侃的,人们不大能看到他和大伙互动,当然也有例外,那便是谈到草药的话题上。三宝没有多少地,种的东西也从不够卖,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头母牛,进行的最多的工作即是山上放牛,牛放的时间长了,家里的柴禾堆的能烧几年,无事可干,他就开始在山上挖草药。
他是喜欢挖草药,但却不大认识,也不大懂药的。他关于药的唯一认知,乃是来源于本地原有的口耳相传及街上卖跌打损伤药的地摊儿。因为,他也无所谓药真不真,有无药效,只是觉得这东西有味道,长得奇特,或者与其他摊子上有几分相似,那边热此不疲地挖回家。
回家后,会挖空心思,按照其形状、气味、大小、生长之地方,按照想象给予安名字。安完名字后,又自编一段神仙道法救死扶伤的故事。一切准备就绪,便骑着他那辆花了五十元买来的三轮自行车,载着满满一斗子东西上街了。
到得街上桥头,东西一放,站在一个台阶上,靠着围栏,瞬间释放出了无穷的光芒,口中滔滔不绝,各种神奇疗效,历史故事,医家传说,张口就来,且极富感染力和真实感,不久竟常有不少人来摊前购买。久而久之,卖草药竟成了他长期的生意和新的身份一种标示。久而久之,三宝自己也对所宣传的搞不清真假了。
有一回他的牛病了,三宝硬是在山上跑了几天挖了各种草药,然后给牛煮了一大锅汤,再合着一些白米粥弄给牛吃,结果这头牛喝了药汤之后,连续三天屙流水泻,拉得肚子干瘪干瘪,连站斗站不起来了,眼看就要挂了。
于是,三宝又对牛特别好,天天给它洗澡照顾,给它喂白米粥喂最嫩最好的草。没想到过了一个来礼拜这牛还就真的好了,不知是药效还是牛自身的免疫力强大,没被折腾死。总之,牛康复了,在三宝认为,这是自己草药有效且方子高明的真实见证。此副让牛拉到虚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方,也成了他压箱底不外传的经典。
其后不久,我家的牛也不愿意吃东西,精神不好。结果,此消息被三宝知道了。某天下午,三宝匆匆跑来我家,说要给我家的牛挖草药治病,并且保证药到病除,立马见效。我们一开始没在意,以为只是玩笑和瞎说。
不曾想,此后他天天上山,拿着镰刀,锄头和小一字镐,再带一点盒饭与水,全副武装就上山了,早上去,天黑了才见他背点草药回来,扁篓里各种奇形怪状,认识不认识的皆有。
一连数日,我家人也无在意,结果有一天早上他忽然又到了我家。背上扛着一大把的各种奇形怪状的草根树根来到我家,一进门就说“哎呀,新华书记,你的牛还没好吧?我上山挖了还几天草药,就是想帮你屋里的牛找到好药来,哎呀这下子好了,我终于挖全了,今天早上给你送过了,保证你的牛喝了这个草药的汤,是药到病除,念念起来作田都不晓得苦”。
我们一家当时一听真是哭笑不得,心里又是感动,又是莫名其妙,又是忍不住肚子里面的笑。可虽明知此药风险不小,断然不能轻易尝试,但是看着他这份真诚、热情且多日的辛苦,不好拒绝。于是,拿出几十元钱强制的要塞给他,一边塞一遍连声的说“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一定试试”。
可是三宝呢,死活不肯接钱,他说“你的钱,我是不会收的,我上山跋涉了几天是看你比我家里的那个老三还更好,做事不会那么过分,不然的话你拿出一千块钱给我都不会卖给你”。好说歹说,钱塞口袋又被扔了出来,还发脾气,说我们看不起他。总之,就是不接钱,推来推去,只好作罢。当然,我们并未敢用他的药,最后找还是他在兽医站工作的大哥,为牛打了针才痊愈。不过,此后他却常在街上同人说,书记家的牛就是吃了他得草药才好起来的。
现在回想,卖药那段时光,或许是三宝人生中最为快意的日子,这构成了我对其更为立体和生动的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发酵到今天,于是,在三宝去世多年后,催生了此文。

前面三宝提到的老三,是他的亲兄弟。从大家族的角度来说,他并非算是孤人,因为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四兄妹中,大哥,小弟,妹夫都算是乡镇一级单位的干部,再加上几个在国企的侄子,一大家子基本都是有身份的公家人,这在本地并不多见,说来也算有权有势的望族。不过,倒个十碗水,不可能碗碗平,大家庭出了个三宝这样的人物。
是的,他是不被兄弟姐妹甚至侄子们待见的,不说平日,单从过年过节就可以看出,虽是住在隔河两岸,直线距离不足四百米,且兄弟都有新房,极不情愿叫他一起过,至多只是象征性的请来吃一餐,或者打包些剩饭剩菜送过去。加之,又是斋公,所以等于只是吃几棵萝卜青菜,魔芋水豆腐啥的。基本上打包过去的,都留给了八九十岁的老母亲,他捞不到一些油水,抑或是本就不在乎这点油水。
但在那两间破旧的几乎要倒塌的土砖房里,两个儿媳除了送饭送菜,剩下的拉撒洗涮倒屎倒尿的具体工作,皆有他主要承担。这是一件说起来是理所应当和本分的工作,却也是极其的吃力不讨好。兄弟姐妹们并未因此对他好一点,乃至看高一分。
他老母亲年轻时又是个极其厉害的女人,哪怕到了瘫痪在床,也依然对这个儿子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昏暗逼仄的房间里,她会随时抓起一切能抓到的东西扔向这个儿子,有时候甚至会忽然坐起来,往他脸上挠一把,似乎是天生的仇人。
三宝隐忍着,一声不吭,既不回手,也不回骂,甚至也没有其他更多的表示。只是在出门放牛时,我们看到他用他竹梢子,发了狠的往那头牛身上抽,每抽一下,牛皮上就肿起来一条痕迹,满牛背的痕迹,不知道是否可以承载他的一些情绪。
就在哪个屋子里,他熬过了二十几年,从老人身体康健能追着他打,到拄着拐杖站在门口骂他,再到瘫痪在床只能抓起手边的东西扔过去,再到老人于九十高龄死去。

母亲死后,那几间老房子也倒了一个角,无人帮忙修缮,住人是不合适了。三宝卖了牛,地也不种了,干脆骑着他的三轮车离开了村庄。游走在附近几个乡镇,一边卖药,一边捡破烂,一边流浪,住过桥下,住过路边,住过涵洞,住过老屋破庙,也住过废弃的楼房。实在太饿时,也找过自己的弟弟和在国企上班的侄子,他守在他们单位门口,报出自己的来历,不过只是得来一两百块钱和几顿盒饭,然后接着消失。
后来,三宝的小弟得急病死了。做香火和七月半烧衣时,收到通知,三宝都回来看过。他回来时是在一个下午,嘎吱嘎吱,吃力的骑着那辆破三轮自行车,一身破破烂烂,比以前显得老了,骑了一路的车,额头上有些汗珠,经过我家门口,我还跟他打了声招呼,要请他喝一杯水,可是三宝谢绝了。
此时三宝的大哥并未因小弟的英年早逝而伤悲,反而因着曾经的一些恩怨而感到快意,优哉游哉,颇有幸灾乐祸感。三宝脸上却反而时有些沉重,甚至是伤悲的。他给老三带了纸钱,但是在他们招呼各种亲朋好友时,三宝成了被忽略得存在。他心知肚明,也未强留,当晚就回老房子里找了几样东西出来,扔到自己的三轮车上,径直的走了。从此几年又没有音讯。
三年后,他得大哥也患癌症去世,听人说三宝也还是回来了,不过是走路回来的,谁也不知他的那辆破三轮是否还在,或者是已经破的没法再骑了。但他的衣衫更旧更黑更脏更破了,头发杂乱带着丛丛白丝,胡须拉碴,满头大汗,身上透着许久不曾洗澡得臭味,手里提着一挂明晃晃金闪闪的纸钱,显目而对比强烈。
三个兄弟,只剩下命最苦的哪一个,他风尘仆仆满脸沧桑的回来,也依旧如上次般,一声不吭,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没有坐一下,没有睡一宿,放下纸钱香烛,看了眼棺材,默默的站了会儿,就走了。这次葬礼后不久,他的大嫂也去世了,这一次他没有回来,当然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人通知他。

我曾问过村里许多人,问他们是否知道三宝的下落,但似乎没人真正说得清。有人说他前几年在山峰仙庵做斋公守庙,有的说他做了叫花子讨钱,也有的说他病死在桥洞下,还有的说他当了真正的和尚。但是至始至终他的这些亲人都没有去找过或者真正得过问过,彷佛他本就不该存在。
我最后听到他得消息大约是在2016年,离他流浪消失已经过去七八年,听说三宝当初的确做过和尚,只是被不知什么人赶了出来。无奈之下,进了敬老院,并且病死在其中,虽然家族颇大,死后却仍是被当着完全得孤人来处理,并无人为其办理后事,他的坟墓也不知道在哪里,或许根本就没有坟吧。
除此之外,我再也不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了,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同在一个村庄生活的人,我对他仍是怀念的。我想当自己百年之后,或许和他并没有多少差别,都是黄土一抔,回归自然。
而此刻再写下这篇不成熟的文字,心里更多的是在体会他一生中所具有的全部孤单和悲伤,体会他在人世间所有的沉浮和悲凉。或许没有意义,或许只是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安好。三宝三宝,若有来生,愿他真成为谁的“宝”。



 朗读本文
朗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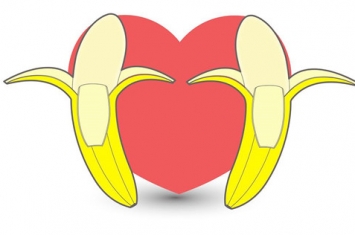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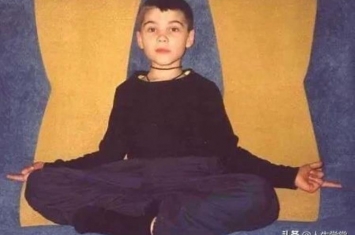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