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元年,为避战乱李姓大户跟着司马皇族南迁,在杭州金陵城落脚,其家居古秦淮只有区区百米,秦淮两岸风光迤逦,歌舞升平,不输东都洛阳,李家有一子名器霖,专务读书,但大族人家多是引荐做官,两晋务空谈,官员多博虚名,倡导黄老之说,迎合无为。
器霖随饱读诗书,但进阶无门,一日午后烦闷,散步秦淮河畔,之间八百里秦淮绝代佳人翩翩公子络绎不绝,香粉美酒处处都有,不仅叹到世风如此,我何为异类乎,其后遍日日留恋歌舞春宫,成为妓院的常客,无奈男人精元有限,日趋枯瘦,但又戒酒戒淫不得,老夫哀叹此子混涨如此,任由他放荡。
一日晚间,器霖去秦淮花船偶遇一绝色女子,女子百般迎合,二人入船而眠,其间云雨不断,酒后睡去,器霖听到有人呼唤,公子再不速速离去,今夕将变女儿身,器霖随即惊醒,微睁开双眼,看到酒桌旁一大汉,驴脸人身,与一黑脸猪身大汉正在私语,吾刚才幻化美人已将其灌醉,猪兄修炼百年,仍无修成男人伟器,带我将器霖公子物件割下,转嫁兄身,祝兄早日体验人间美事,器霖听到此,汗流浃背,窗外月光煞白,更加寒意,这时耳边又有人语,吾欲助公子脱身,忘公子记住,淫为万恶之首,回家后当专心读书,伺候父母,保你无忧,他日定当入宦门。器霖心里默应。
不过片刻,窗外寒光闪过,两只金蜈蚣分别咬住驴脸和猪身大汉,须臾之间现出原形,为一头黑驴和一头老猪。
器霖经此一劫,翻然悔悟,后入军门,做到御史台中丞。
奉劝世人,万恶淫为首,道法自然。
欢迎各位关注指导评论转发点赞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好清谈,而不做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清谈呢?与现代喝酒划拳还喝茶调情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些士为什么好清谈而不做事呢。对于清谈,他们自己什么态度呢。清谈为后世留下了什么呢。清谈起源于东汉末年,当时确实是出于躲避迫害三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翻身做主人西晋开始,清谈家掌握了朝政大权热衷于营私、不问国事,清谈家对西晋灭亡负有重大责任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崛起,皇权已成为强弩之末。但是在这种政治随时面临崩盘的情况下,各地却分权而立,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
而此时曹魏政权奉行“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给出生低微的有才之士打开了一扇窗,众多寒门学子凭借文采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极大的刺激了文士们的创作。一时间,社会风气大开,文学创作获得了良好的生长土壤,文坛开始活跃起来,开创了文学创作史上的“大繁荣景象”。这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被誉为“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把柔软流动之风与坚硬强健之骨结合起来,刚柔并济,反映了建安时期的文人的创作特色,这一时期的文人怀抱着济世安民的热情,在文中抒发着自己的忧国忧民、热心朝政的意识,风格大多刚健有力、热情澎湃,如曹操的《短歌行》。而魏晋风度作为与建安风骨紧紧衔接的一个时代特色,可以看作是建安风骨的延申,却在短短百年的时间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魏晋多名士,大多洒脱率性而不拘小节,从容貌而言,大多风度翩翩,形神肃立;但行为举止而言,却是沉迷药酒、行为放荡。
当然,谈到魏晋名士无法避开的就是“清谈”之风,所谓清谈,谈什么?为何名士皆尚清谈?
一、儒家思想的崩塌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世家大族崛起。当时数的上名号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世家大族权倾朝野,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倚仗自己的权势占地为王。而地主豪强也绝对不闲着,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断进行土地兼并,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此时朝野中手握兵权的武将蠢蠢欲动,社会面临分崩离析。在稳定时期发挥管理民众作用的儒学此时显得大而无用。
中央政府积弊深重,社会时局混乱。在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此时开始摇摇欲坠,而谶纬之学在这样的乱局中也频频失效。一时间,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怀疑其真实性,对于儒学的怀疑让他们冷静下来,他们不再简单的迷信儒学的空洞说教,连同着对于从前深信不疑的谶纬之学也有了新的思考。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心灵窗口,来解决现在所处时代的实际问题,此时“玄学”应运而生。
从前的儒学讲究“三纲五常”,对于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但乱局下的社会秩序已经被完全打破,这些陈词滥调显然不再适用于乱世,这一时期的知识知识分子开始从哲学的眼光去思考社会问题,即玄学,亦称新道家。他们崇尚老子的思想,玄学的名字也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围绕着围绕《周易》、《老子》、《庄子》等玄妙深奥的话题展开辩论,称之为“清谈”(也叫“玄谈”)。当时的清谈可谓笼络天下名士,如历史上又名的谢安、王导,即是在朝高官,又是清谈高手。

二、士大夫莫谈国事
司马懿一生机关算尽,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强大汉朝最后一线荣光降落之际,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位。他的上位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街头巷尾窃窃私语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司马家族深知其中道理,所以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堵上民众地嘴。司马家族对于士族阶层采取严格的舆论控制,并且做出了具体行动,司马懿诛杀曹爽等,并夷其三族,又诛杀名士何晏,后司马师又杀死夏侯玄,面对如此血腥的残杀,让草根阶层的民众和身居高位的世家大族都人人自危,唯恐成为司马家族诛杀的对象,从上到下,各阶层胆战心惊、噤若寒蝉。
而这些名士面对如此惨烈的屠杀,对统治者极度心寒,放弃参与朝政选择归隐山林,与众好友饮酒作乐、吟诗弹唱,其中不乏又个性出挑之人、行为出格知识,如饮酒狂人刘伶常狂饮不止,抬棺狂欢。而阮籍常与邻家女掌柜饮酒,醉倒之后便睡在其旁。这些行为放纵出格、有悖纲常,放到现代也是难以理解的行为,但在当时竟然在名士当中蔚然成风。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皇权凌厉对人格的极度压迫,这些名士无处抒发,在不断压抑自我的精神信仰中痛苦求生,最终放荡訾睢、无所顾忌。
此时的司马家族仍然延续以往的“九品中正制”,此制度分为家世、行状、定品三个方面,起初解决了管理选拔没有定准的问题,但到西晋,这种制度已经被世家大族所掌控,出生寒门的人行状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也能定在上品,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寒门读书人失去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只能崇尚清谈。

三、清谈的内容
所谓清谈,如何清谈?从何而谈?
清谈,一般或为两人,或为三人,或为多人组成,他们一边喝茶饮酒,一边畅所欲言,针对某个话题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而其讨论的终极问题则是关于有和无的问题。从正始清谈开始直至后世的竹林清谈,清谈在名士之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才思以及文学造诣的彰显,更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几乎成为了名士的必备技能之一。
清谈的场面也是十分激烈的,此时,这些游离于朝政之外以避朝廷锋芒的名士将自己的注意力尽皆集中于哲学问题的终极思考上,他们围绕着《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内容展开,分为宾主双方,围绕一个问题,反复探究其来龙去脉,主客双方往往是针锋相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想将对方辩倒,而到激烈之时,他们还会手舞足蹈,口吐粗言,忘乎所以。等到本场清谈结束后,若主客双方达成一致,则握手言和;若依旧各执一辞,就请第三方来为本场清谈做出总结性发言,之后则约好下次再论,直到对方心服口服为止。
当然,清谈对于文人墨客而言,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更是一种可以抒发情怀、展现自我才华的手段,通过清谈,文人们可以向其他文人展示出自己真正的才华,成为他人仰慕的存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士在清谈的过程中往往“盛饰麈尾。”所谓麈尾行状有点像树叶,类似于羽毛,但比羽毛更硬,可以直立起来,挥动麈尾会伴随清风拂面。在清谈之际,一边口若悬河,一边轻摇麈尾,可谓清雅至极。
魏晋时期,清谈成风,此时文人墨客们只需一盏清茶,一杯醇酒,就可天马行空般的喋喋不休。这时,就连女性和小孩也会参与其中,比如某一次,王献之与人谈论诗文,疲于应付,被人说的是狼狈不堪,此时躲在青帘之后的嫂子谢道韫听到,忍不住谈兴大发,接着话题,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工夫,与王献之清谈的文人们就无言以对,理屈词穷,甘拜下风。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裴遐娶了太尉王衍的第四个女儿,新婚刚满三日,几个女婿就聚集到一起谈话,当时的一些名士以及王、裴两家的族人子弟都到了。西晋著名的玄学家郭象在客座上率先于裴遐发起清谈,郭象学富五车,一开始剑拔弩张、气势逼人,前袁遐几个回合略败下风,但他却从容不迫,还是娓娓道来,议论的义理和情志都显得精深微妙。满座宾客都赞叹叫好。王衍对自己女婿不俗的表现十分满意。
在这些名士的身体力行之下,清谈之风愈演愈烈。西晋时期,曾有一次空谈的盛象,据《世说新语》记载,名士们在洛水游玩,回来的时候,尚书令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王衍说裴仆射擅长谈名理,滔滔不绝,意趣高雅;张茂先谈《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安丰谈论延陵、子房,也极为奥妙。透彻,超尘拔俗。这段记载里包含了几位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我们也可从这几句话中窥见当时的清谈所谈论的内容,其中包含了玄学名理、史书正传等广阔内容。
清谈之风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曾盛行一时,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他是文人在生存危机下对自我心灵的放逐,对后世的影响有利有弊。清谈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涌现除了一批优秀文人,如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对于哲学思想以及文化的繁荣犹是功不可没。但后世历来有人评判清谈误国,就连西晋名士王衍素来擅长于清谈,人称“口中雌黄”,在被石勒杀死之前,也发出“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的慨叹,但将误国一事尽推于清谈之上未免也有失偏颇。

有人把魏晋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礼仪之邦的古老中古在这一时期首次冲破了伦理纲常的限制,纷纷崇尚名士风流,扪虱座谈、纵情饮酒、声色犬马等一度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对象。然而其实这也是历史上文人面临的最为黑暗的一个寒冬,这些看似出格放纵的事情背后实则隐藏的是魏晋名士不堪一击的政治理想、以及惶惑不安的脆弱命途,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名士们在怀抱满腔热血却被黑暗现实冰封之后,只能寄情于无所作用的清谈。
总得说,由于清谈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属于虚无之论,仅为士大夫和文人们消遣,及显示清高的一种方式,于国于民皆是毫无意义。正所谓“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清谈就是一场自吹自话的一场讨论会罢了,其所谈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空话,若是放到实际,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好清谈,而不做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清谈呢?与现代喝酒划拳还喝茶调情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些士为什么好清谈而不做事呢。对于清谈,他们自己什么态度呢。清谈为后世留下了什么呢。清谈起源于东汉末年,当时确实是出于躲避迫害三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翻身做主人西晋开始,清谈家掌握了朝政大权热衷于营私、不问国事,清谈家对西晋灭亡负有重大责任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崛起,皇权已成为强弩之末。但是在这种政治随时面临崩盘的情况下,各地却分权而立,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
而此时曹魏政权奉行“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给出生低微的有才之士打开了一扇窗,众多寒门学子凭借文采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极大的刺激了文士们的创作。一时间,社会风气大开,文学创作获得了良好的生长土壤,文坛开始活跃起来,开创了文学创作史上的“大繁荣景象”。这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被誉为“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把柔软流动之风与坚硬强健之骨结合起来,刚柔并济,反映了建安时期的文人的创作特色,这一时期的文人怀抱着济世安民的热情,在文中抒发着自己的忧国忧民、热心朝政的意识,风格大多刚健有力、热情澎湃,如曹操的《短歌行》。而魏晋风度作为与建安风骨紧紧衔接的一个时代特色,可以看作是建安风骨的延申,却在短短百年的时间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魏晋多名士,大多洒脱率性而不拘小节,从容貌而言,大多风度翩翩,形神肃立;但行为举止而言,却是沉迷药酒、行为放荡。
当然,谈到魏晋名士无法避开的就是“清谈”之风,所谓清谈,谈什么?为何名士皆尚清谈?
一、儒家思想的崩塌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世家大族崛起。当时数的上名号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世家大族权倾朝野,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倚仗自己的权势占地为王。而地主豪强也绝对不闲着,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断进行土地兼并,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此时朝野中手握兵权的武将蠢蠢欲动,社会面临分崩离析。在稳定时期发挥管理民众作用的儒学此时显得大而无用。
中央政府积弊深重,社会时局混乱。在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此时开始摇摇欲坠,而谶纬之学在这样的乱局中也频频失效。一时间,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怀疑其真实性,对于儒学的怀疑让他们冷静下来,他们不再简单的迷信儒学的空洞说教,连同着对于从前深信不疑的谶纬之学也有了新的思考。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心灵窗口,来解决现在所处时代的实际问题,此时“玄学”应运而生。
从前的儒学讲究“三纲五常”,对于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但乱局下的社会秩序已经被完全打破,这些陈词滥调显然不再适用于乱世,这一时期的知识知识分子开始从哲学的眼光去思考社会问题,即玄学,亦称新道家。他们崇尚老子的思想,玄学的名字也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围绕着围绕《周易》、《老子》、《庄子》等玄妙深奥的话题展开辩论,称之为“清谈”(也叫“玄谈”)。当时的清谈可谓笼络天下名士,如历史上又名的谢安、王导,即是在朝高官,又是清谈高手。

二、士大夫莫谈国事
司马懿一生机关算尽,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强大汉朝最后一线荣光降落之际,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位。他的上位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街头巷尾窃窃私语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司马家族深知其中道理,所以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堵上民众地嘴。司马家族对于士族阶层采取严格的舆论控制,并且做出了具体行动,司马懿诛杀曹爽等,并夷其三族,又诛杀名士何晏,后司马师又杀死夏侯玄,面对如此血腥的残杀,让草根阶层的民众和身居高位的世家大族都人人自危,唯恐成为司马家族诛杀的对象,从上到下,各阶层胆战心惊、噤若寒蝉。
而这些名士面对如此惨烈的屠杀,对统治者极度心寒,放弃参与朝政选择归隐山林,与众好友饮酒作乐、吟诗弹唱,其中不乏又个性出挑之人、行为出格知识,如饮酒狂人刘伶常狂饮不止,抬棺狂欢。而阮籍常与邻家女掌柜饮酒,醉倒之后便睡在其旁。这些行为放纵出格、有悖纲常,放到现代也是难以理解的行为,但在当时竟然在名士当中蔚然成风。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皇权凌厉对人格的极度压迫,这些名士无处抒发,在不断压抑自我的精神信仰中痛苦求生,最终放荡訾睢、无所顾忌。
此时的司马家族仍然延续以往的“九品中正制”,此制度分为家世、行状、定品三个方面,起初解决了管理选拔没有定准的问题,但到西晋,这种制度已经被世家大族所掌控,出生寒门的人行状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也能定在上品,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寒门读书人失去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只能崇尚清谈。

三、清谈的内容
所谓清谈,如何清谈?从何而谈?
清谈,一般或为两人,或为三人,或为多人组成,他们一边喝茶饮酒,一边畅所欲言,针对某个话题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而其讨论的终极问题则是关于有和无的问题。从正始清谈开始直至后世的竹林清谈,清谈在名士之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才思以及文学造诣的彰显,更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几乎成为了名士的必备技能之一。
清谈的场面也是十分激烈的,此时,这些游离于朝政之外以避朝廷锋芒的名士将自己的注意力尽皆集中于哲学问题的终极思考上,他们围绕着《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内容展开,分为宾主双方,围绕一个问题,反复探究其来龙去脉,主客双方往往是针锋相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想将对方辩倒,而到激烈之时,他们还会手舞足蹈,口吐粗言,忘乎所以。等到本场清谈结束后,若主客双方达成一致,则握手言和;若依旧各执一辞,就请第三方来为本场清谈做出总结性发言,之后则约好下次再论,直到对方心服口服为止。
当然,清谈对于文人墨客而言,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更是一种可以抒发情怀、展现自我才华的手段,通过清谈,文人们可以向其他文人展示出自己真正的才华,成为他人仰慕的存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士在清谈的过程中往往“盛饰麈尾。”所谓麈尾行状有点像树叶,类似于羽毛,但比羽毛更硬,可以直立起来,挥动麈尾会伴随清风拂面。在清谈之际,一边口若悬河,一边轻摇麈尾,可谓清雅至极。
魏晋时期,清谈成风,此时文人墨客们只需一盏清茶,一杯醇酒,就可天马行空般的喋喋不休。这时,就连女性和小孩也会参与其中,比如某一次,王献之与人谈论诗文,疲于应付,被人说的是狼狈不堪,此时躲在青帘之后的嫂子谢道韫听到,忍不住谈兴大发,接着话题,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工夫,与王献之清谈的文人们就无言以对,理屈词穷,甘拜下风。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裴遐娶了太尉王衍的第四个女儿,新婚刚满三日,几个女婿就聚集到一起谈话,当时的一些名士以及王、裴两家的族人子弟都到了。西晋著名的玄学家郭象在客座上率先于裴遐发起清谈,郭象学富五车,一开始剑拔弩张、气势逼人,前袁遐几个回合略败下风,但他却从容不迫,还是娓娓道来,议论的义理和情志都显得精深微妙。满座宾客都赞叹叫好。王衍对自己女婿不俗的表现十分满意。
在这些名士的身体力行之下,清谈之风愈演愈烈。西晋时期,曾有一次空谈的盛象,据《世说新语》记载,名士们在洛水游玩,回来的时候,尚书令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王衍说裴仆射擅长谈名理,滔滔不绝,意趣高雅;张茂先谈《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安丰谈论延陵、子房,也极为奥妙。透彻,超尘拔俗。这段记载里包含了几位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我们也可从这几句话中窥见当时的清谈所谈论的内容,其中包含了玄学名理、史书正传等广阔内容。
清谈之风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曾盛行一时,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他是文人在生存危机下对自我心灵的放逐,对后世的影响有利有弊。清谈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涌现除了一批优秀文人,如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对于哲学思想以及文化的繁荣犹是功不可没。但后世历来有人评判清谈误国,就连西晋名士王衍素来擅长于清谈,人称“口中雌黄”,在被石勒杀死之前,也发出“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的慨叹,但将误国一事尽推于清谈之上未免也有失偏颇。

有人把魏晋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礼仪之邦的古老中古在这一时期首次冲破了伦理纲常的限制,纷纷崇尚名士风流,扪虱座谈、纵情饮酒、声色犬马等一度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对象。然而其实这也是历史上文人面临的最为黑暗的一个寒冬,这些看似出格放纵的事情背后实则隐藏的是魏晋名士不堪一击的政治理想、以及惶惑不安的脆弱命途,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名士们在怀抱满腔热血却被黑暗现实冰封之后,只能寄情于无所作用的清谈。
总得说,由于清谈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属于虚无之论,仅为士大夫和文人们消遣,及显示清高的一种方式,于国于民皆是毫无意义。正所谓“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清谈就是一场自吹自话的一场讨论会罢了,其所谈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空话,若是放到实际,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好清谈,而不做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清谈呢?与现代喝酒划拳还喝茶调情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些士为什么好清谈而不做事呢。对于清谈,他们自己什么态度呢。清谈为后世留下了什么呢。清谈起源于东汉末年,当时确实是出于躲避迫害三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翻身做主人西晋开始,清谈家掌握了朝政大权热衷于营私、不问国事,清谈家对西晋灭亡负有重大责任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崛起,皇权已成为强弩之末。但是在这种政治随时面临崩盘的情况下,各地却分权而立,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
而此时曹魏政权奉行“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给出生低微的有才之士打开了一扇窗,众多寒门学子凭借文采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极大的刺激了文士们的创作。一时间,社会风气大开,文学创作获得了良好的生长土壤,文坛开始活跃起来,开创了文学创作史上的“大繁荣景象”。这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被誉为“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把柔软流动之风与坚硬强健之骨结合起来,刚柔并济,反映了建安时期的文人的创作特色,这一时期的文人怀抱着济世安民的热情,在文中抒发着自己的忧国忧民、热心朝政的意识,风格大多刚健有力、热情澎湃,如曹操的《短歌行》。而魏晋风度作为与建安风骨紧紧衔接的一个时代特色,可以看作是建安风骨的延申,却在短短百年的时间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魏晋多名士,大多洒脱率性而不拘小节,从容貌而言,大多风度翩翩,形神肃立;但行为举止而言,却是沉迷药酒、行为放荡。
当然,谈到魏晋名士无法避开的就是“清谈”之风,所谓清谈,谈什么?为何名士皆尚清谈?
一、儒家思想的崩塌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世家大族崛起。当时数的上名号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世家大族权倾朝野,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倚仗自己的权势占地为王。而地主豪强也绝对不闲着,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断进行土地兼并,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此时朝野中手握兵权的武将蠢蠢欲动,社会面临分崩离析。在稳定时期发挥管理民众作用的儒学此时显得大而无用。
中央政府积弊深重,社会时局混乱。在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此时开始摇摇欲坠,而谶纬之学在这样的乱局中也频频失效。一时间,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怀疑其真实性,对于儒学的怀疑让他们冷静下来,他们不再简单的迷信儒学的空洞说教,连同着对于从前深信不疑的谶纬之学也有了新的思考。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心灵窗口,来解决现在所处时代的实际问题,此时“玄学”应运而生。
从前的儒学讲究“三纲五常”,对于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但乱局下的社会秩序已经被完全打破,这些陈词滥调显然不再适用于乱世,这一时期的知识知识分子开始从哲学的眼光去思考社会问题,即玄学,亦称新道家。他们崇尚老子的思想,玄学的名字也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围绕着围绕《周易》、《老子》、《庄子》等玄妙深奥的话题展开辩论,称之为“清谈”(也叫“玄谈”)。当时的清谈可谓笼络天下名士,如历史上又名的谢安、王导,即是在朝高官,又是清谈高手。

二、士大夫莫谈国事
司马懿一生机关算尽,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强大汉朝最后一线荣光降落之际,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位。他的上位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街头巷尾窃窃私语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司马家族深知其中道理,所以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堵上民众地嘴。司马家族对于士族阶层采取严格的舆论控制,并且做出了具体行动,司马懿诛杀曹爽等,并夷其三族,又诛杀名士何晏,后司马师又杀死夏侯玄,面对如此血腥的残杀,让草根阶层的民众和身居高位的世家大族都人人自危,唯恐成为司马家族诛杀的对象,从上到下,各阶层胆战心惊、噤若寒蝉。
而这些名士面对如此惨烈的屠杀,对统治者极度心寒,放弃参与朝政选择归隐山林,与众好友饮酒作乐、吟诗弹唱,其中不乏又个性出挑之人、行为出格知识,如饮酒狂人刘伶常狂饮不止,抬棺狂欢。而阮籍常与邻家女掌柜饮酒,醉倒之后便睡在其旁。这些行为放纵出格、有悖纲常,放到现代也是难以理解的行为,但在当时竟然在名士当中蔚然成风。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皇权凌厉对人格的极度压迫,这些名士无处抒发,在不断压抑自我的精神信仰中痛苦求生,最终放荡訾睢、无所顾忌。
此时的司马家族仍然延续以往的“九品中正制”,此制度分为家世、行状、定品三个方面,起初解决了管理选拔没有定准的问题,但到西晋,这种制度已经被世家大族所掌控,出生寒门的人行状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也能定在上品,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寒门读书人失去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只能崇尚清谈。

三、清谈的内容
所谓清谈,如何清谈?从何而谈?
清谈,一般或为两人,或为三人,或为多人组成,他们一边喝茶饮酒,一边畅所欲言,针对某个话题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而其讨论的终极问题则是关于有和无的问题。从正始清谈开始直至后世的竹林清谈,清谈在名士之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才思以及文学造诣的彰显,更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几乎成为了名士的必备技能之一。
清谈的场面也是十分激烈的,此时,这些游离于朝政之外以避朝廷锋芒的名士将自己的注意力尽皆集中于哲学问题的终极思考上,他们围绕着《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内容展开,分为宾主双方,围绕一个问题,反复探究其来龙去脉,主客双方往往是针锋相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想将对方辩倒,而到激烈之时,他们还会手舞足蹈,口吐粗言,忘乎所以。等到本场清谈结束后,若主客双方达成一致,则握手言和;若依旧各执一辞,就请第三方来为本场清谈做出总结性发言,之后则约好下次再论,直到对方心服口服为止。
当然,清谈对于文人墨客而言,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更是一种可以抒发情怀、展现自我才华的手段,通过清谈,文人们可以向其他文人展示出自己真正的才华,成为他人仰慕的存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士在清谈的过程中往往“盛饰麈尾。”所谓麈尾行状有点像树叶,类似于羽毛,但比羽毛更硬,可以直立起来,挥动麈尾会伴随清风拂面。在清谈之际,一边口若悬河,一边轻摇麈尾,可谓清雅至极。
魏晋时期,清谈成风,此时文人墨客们只需一盏清茶,一杯醇酒,就可天马行空般的喋喋不休。这时,就连女性和小孩也会参与其中,比如某一次,王献之与人谈论诗文,疲于应付,被人说的是狼狈不堪,此时躲在青帘之后的嫂子谢道韫听到,忍不住谈兴大发,接着话题,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工夫,与王献之清谈的文人们就无言以对,理屈词穷,甘拜下风。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裴遐娶了太尉王衍的第四个女儿,新婚刚满三日,几个女婿就聚集到一起谈话,当时的一些名士以及王、裴两家的族人子弟都到了。西晋著名的玄学家郭象在客座上率先于裴遐发起清谈,郭象学富五车,一开始剑拔弩张、气势逼人,前袁遐几个回合略败下风,但他却从容不迫,还是娓娓道来,议论的义理和情志都显得精深微妙。满座宾客都赞叹叫好。王衍对自己女婿不俗的表现十分满意。
在这些名士的身体力行之下,清谈之风愈演愈烈。西晋时期,曾有一次空谈的盛象,据《世说新语》记载,名士们在洛水游玩,回来的时候,尚书令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王衍说裴仆射擅长谈名理,滔滔不绝,意趣高雅;张茂先谈《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安丰谈论延陵、子房,也极为奥妙。透彻,超尘拔俗。这段记载里包含了几位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我们也可从这几句话中窥见当时的清谈所谈论的内容,其中包含了玄学名理、史书正传等广阔内容。
清谈之风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曾盛行一时,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他是文人在生存危机下对自我心灵的放逐,对后世的影响有利有弊。清谈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涌现除了一批优秀文人,如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对于哲学思想以及文化的繁荣犹是功不可没。但后世历来有人评判清谈误国,就连西晋名士王衍素来擅长于清谈,人称“口中雌黄”,在被石勒杀死之前,也发出“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的慨叹,但将误国一事尽推于清谈之上未免也有失偏颇。

有人把魏晋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礼仪之邦的古老中古在这一时期首次冲破了伦理纲常的限制,纷纷崇尚名士风流,扪虱座谈、纵情饮酒、声色犬马等一度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对象。然而其实这也是历史上文人面临的最为黑暗的一个寒冬,这些看似出格放纵的事情背后实则隐藏的是魏晋名士不堪一击的政治理想、以及惶惑不安的脆弱命途,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名士们在怀抱满腔热血却被黑暗现实冰封之后,只能寄情于无所作用的清谈。
总得说,由于清谈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属于虚无之论,仅为士大夫和文人们消遣,及显示清高的一种方式,于国于民皆是毫无意义。正所谓“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清谈就是一场自吹自话的一场讨论会罢了,其所谈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空话,若是放到实际,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好清谈,而不做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清谈呢?与现代喝酒划拳还喝茶调情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些士为什么好清谈而不做事呢。对于清谈,他们自己什么态度呢。清谈为后世留下了什么呢。清谈起源于东汉末年,当时确实是出于躲避迫害三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翻身做主人西晋开始,清谈家掌握了朝政大权热衷于营私、不问国事,清谈家对西晋灭亡负有重大责任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崛起,皇权已成为强弩之末。但是在这种政治随时面临崩盘的情况下,各地却分权而立,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
而此时曹魏政权奉行“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给出生低微的有才之士打开了一扇窗,众多寒门学子凭借文采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极大的刺激了文士们的创作。一时间,社会风气大开,文学创作获得了良好的生长土壤,文坛开始活跃起来,开创了文学创作史上的“大繁荣景象”。这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被誉为“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把柔软流动之风与坚硬强健之骨结合起来,刚柔并济,反映了建安时期的文人的创作特色,这一时期的文人怀抱着济世安民的热情,在文中抒发着自己的忧国忧民、热心朝政的意识,风格大多刚健有力、热情澎湃,如曹操的《短歌行》。而魏晋风度作为与建安风骨紧紧衔接的一个时代特色,可以看作是建安风骨的延申,却在短短百年的时间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魏晋多名士,大多洒脱率性而不拘小节,从容貌而言,大多风度翩翩,形神肃立;但行为举止而言,却是沉迷药酒、行为放荡。
当然,谈到魏晋名士无法避开的就是“清谈”之风,所谓清谈,谈什么?为何名士皆尚清谈?
一、儒家思想的崩塌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世家大族崛起。当时数的上名号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世家大族权倾朝野,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倚仗自己的权势占地为王。而地主豪强也绝对不闲着,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断进行土地兼并,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此时朝野中手握兵权的武将蠢蠢欲动,社会面临分崩离析。在稳定时期发挥管理民众作用的儒学此时显得大而无用。
中央政府积弊深重,社会时局混乱。在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此时开始摇摇欲坠,而谶纬之学在这样的乱局中也频频失效。一时间,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怀疑其真实性,对于儒学的怀疑让他们冷静下来,他们不再简单的迷信儒学的空洞说教,连同着对于从前深信不疑的谶纬之学也有了新的思考。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心灵窗口,来解决现在所处时代的实际问题,此时“玄学”应运而生。
从前的儒学讲究“三纲五常”,对于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但乱局下的社会秩序已经被完全打破,这些陈词滥调显然不再适用于乱世,这一时期的知识知识分子开始从哲学的眼光去思考社会问题,即玄学,亦称新道家。他们崇尚老子的思想,玄学的名字也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围绕着围绕《周易》、《老子》、《庄子》等玄妙深奥的话题展开辩论,称之为“清谈”(也叫“玄谈”)。当时的清谈可谓笼络天下名士,如历史上又名的谢安、王导,即是在朝高官,又是清谈高手。

二、士大夫莫谈国事
司马懿一生机关算尽,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强大汉朝最后一线荣光降落之际,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位。他的上位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街头巷尾窃窃私语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司马家族深知其中道理,所以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堵上民众地嘴。司马家族对于士族阶层采取严格的舆论控制,并且做出了具体行动,司马懿诛杀曹爽等,并夷其三族,又诛杀名士何晏,后司马师又杀死夏侯玄,面对如此血腥的残杀,让草根阶层的民众和身居高位的世家大族都人人自危,唯恐成为司马家族诛杀的对象,从上到下,各阶层胆战心惊、噤若寒蝉。
而这些名士面对如此惨烈的屠杀,对统治者极度心寒,放弃参与朝政选择归隐山林,与众好友饮酒作乐、吟诗弹唱,其中不乏又个性出挑之人、行为出格知识,如饮酒狂人刘伶常狂饮不止,抬棺狂欢。而阮籍常与邻家女掌柜饮酒,醉倒之后便睡在其旁。这些行为放纵出格、有悖纲常,放到现代也是难以理解的行为,但在当时竟然在名士当中蔚然成风。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皇权凌厉对人格的极度压迫,这些名士无处抒发,在不断压抑自我的精神信仰中痛苦求生,最终放荡訾睢、无所顾忌。
此时的司马家族仍然延续以往的“九品中正制”,此制度分为家世、行状、定品三个方面,起初解决了管理选拔没有定准的问题,但到西晋,这种制度已经被世家大族所掌控,出生寒门的人行状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也能定在上品,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寒门读书人失去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只能崇尚清谈。

三、清谈的内容
所谓清谈,如何清谈?从何而谈?
清谈,一般或为两人,或为三人,或为多人组成,他们一边喝茶饮酒,一边畅所欲言,针对某个话题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而其讨论的终极问题则是关于有和无的问题。从正始清谈开始直至后世的竹林清谈,清谈在名士之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才思以及文学造诣的彰显,更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几乎成为了名士的必备技能之一。
清谈的场面也是十分激烈的,此时,这些游离于朝政之外以避朝廷锋芒的名士将自己的注意力尽皆集中于哲学问题的终极思考上,他们围绕着《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内容展开,分为宾主双方,围绕一个问题,反复探究其来龙去脉,主客双方往往是针锋相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想将对方辩倒,而到激烈之时,他们还会手舞足蹈,口吐粗言,忘乎所以。等到本场清谈结束后,若主客双方达成一致,则握手言和;若依旧各执一辞,就请第三方来为本场清谈做出总结性发言,之后则约好下次再论,直到对方心服口服为止。
当然,清谈对于文人墨客而言,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更是一种可以抒发情怀、展现自我才华的手段,通过清谈,文人们可以向其他文人展示出自己真正的才华,成为他人仰慕的存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士在清谈的过程中往往“盛饰麈尾。”所谓麈尾行状有点像树叶,类似于羽毛,但比羽毛更硬,可以直立起来,挥动麈尾会伴随清风拂面。在清谈之际,一边口若悬河,一边轻摇麈尾,可谓清雅至极。
魏晋时期,清谈成风,此时文人墨客们只需一盏清茶,一杯醇酒,就可天马行空般的喋喋不休。这时,就连女性和小孩也会参与其中,比如某一次,王献之与人谈论诗文,疲于应付,被人说的是狼狈不堪,此时躲在青帘之后的嫂子谢道韫听到,忍不住谈兴大发,接着话题,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工夫,与王献之清谈的文人们就无言以对,理屈词穷,甘拜下风。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裴遐娶了太尉王衍的第四个女儿,新婚刚满三日,几个女婿就聚集到一起谈话,当时的一些名士以及王、裴两家的族人子弟都到了。西晋著名的玄学家郭象在客座上率先于裴遐发起清谈,郭象学富五车,一开始剑拔弩张、气势逼人,前袁遐几个回合略败下风,但他却从容不迫,还是娓娓道来,议论的义理和情志都显得精深微妙。满座宾客都赞叹叫好。王衍对自己女婿不俗的表现十分满意。
在这些名士的身体力行之下,清谈之风愈演愈烈。西晋时期,曾有一次空谈的盛象,据《世说新语》记载,名士们在洛水游玩,回来的时候,尚书令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王衍说裴仆射擅长谈名理,滔滔不绝,意趣高雅;张茂先谈《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安丰谈论延陵、子房,也极为奥妙。透彻,超尘拔俗。这段记载里包含了几位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我们也可从这几句话中窥见当时的清谈所谈论的内容,其中包含了玄学名理、史书正传等广阔内容。
清谈之风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曾盛行一时,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他是文人在生存危机下对自我心灵的放逐,对后世的影响有利有弊。清谈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涌现除了一批优秀文人,如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对于哲学思想以及文化的繁荣犹是功不可没。但后世历来有人评判清谈误国,就连西晋名士王衍素来擅长于清谈,人称“口中雌黄”,在被石勒杀死之前,也发出“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的慨叹,但将误国一事尽推于清谈之上未免也有失偏颇。

有人把魏晋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礼仪之邦的古老中古在这一时期首次冲破了伦理纲常的限制,纷纷崇尚名士风流,扪虱座谈、纵情饮酒、声色犬马等一度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对象。然而其实这也是历史上文人面临的最为黑暗的一个寒冬,这些看似出格放纵的事情背后实则隐藏的是魏晋名士不堪一击的政治理想、以及惶惑不安的脆弱命途,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名士们在怀抱满腔热血却被黑暗现实冰封之后,只能寄情于无所作用的清谈。
总得说,由于清谈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属于虚无之论,仅为士大夫和文人们消遣,及显示清高的一种方式,于国于民皆是毫无意义。正所谓“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清谈就是一场自吹自话的一场讨论会罢了,其所谈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空话,若是放到实际,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好清谈,而不做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清谈呢?与现代喝酒划拳还喝茶调情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些士为什么好清谈而不做事呢。对于清谈,他们自己什么态度呢。清谈为后世留下了什么呢。清谈起源于东汉末年,当时确实是出于躲避迫害三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翻身做主人西晋开始,清谈家掌握了朝政大权热衷于营私、不问国事,清谈家对西晋灭亡负有重大责任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崛起,皇权已成为强弩之末。但是在这种政治随时面临崩盘的情况下,各地却分权而立,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
而此时曹魏政权奉行“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给出生低微的有才之士打开了一扇窗,众多寒门学子凭借文采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极大的刺激了文士们的创作。一时间,社会风气大开,文学创作获得了良好的生长土壤,文坛开始活跃起来,开创了文学创作史上的“大繁荣景象”。这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被誉为“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把柔软流动之风与坚硬强健之骨结合起来,刚柔并济,反映了建安时期的文人的创作特色,这一时期的文人怀抱着济世安民的热情,在文中抒发着自己的忧国忧民、热心朝政的意识,风格大多刚健有力、热情澎湃,如曹操的《短歌行》。而魏晋风度作为与建安风骨紧紧衔接的一个时代特色,可以看作是建安风骨的延申,却在短短百年的时间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魏晋多名士,大多洒脱率性而不拘小节,从容貌而言,大多风度翩翩,形神肃立;但行为举止而言,却是沉迷药酒、行为放荡。
当然,谈到魏晋名士无法避开的就是“清谈”之风,所谓清谈,谈什么?为何名士皆尚清谈?
一、儒家思想的崩塌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世家大族崛起。当时数的上名号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世家大族权倾朝野,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倚仗自己的权势占地为王。而地主豪强也绝对不闲着,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断进行土地兼并,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此时朝野中手握兵权的武将蠢蠢欲动,社会面临分崩离析。在稳定时期发挥管理民众作用的儒学此时显得大而无用。
中央政府积弊深重,社会时局混乱。在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此时开始摇摇欲坠,而谶纬之学在这样的乱局中也频频失效。一时间,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怀疑其真实性,对于儒学的怀疑让他们冷静下来,他们不再简单的迷信儒学的空洞说教,连同着对于从前深信不疑的谶纬之学也有了新的思考。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心灵窗口,来解决现在所处时代的实际问题,此时“玄学”应运而生。
从前的儒学讲究“三纲五常”,对于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但乱局下的社会秩序已经被完全打破,这些陈词滥调显然不再适用于乱世,这一时期的知识知识分子开始从哲学的眼光去思考社会问题,即玄学,亦称新道家。他们崇尚老子的思想,玄学的名字也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围绕着围绕《周易》、《老子》、《庄子》等玄妙深奥的话题展开辩论,称之为“清谈”(也叫“玄谈”)。当时的清谈可谓笼络天下名士,如历史上又名的谢安、王导,即是在朝高官,又是清谈高手。

二、士大夫莫谈国事
司马懿一生机关算尽,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强大汉朝最后一线荣光降落之际,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位。他的上位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街头巷尾窃窃私语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司马家族深知其中道理,所以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堵上民众地嘴。司马家族对于士族阶层采取严格的舆论控制,并且做出了具体行动,司马懿诛杀曹爽等,并夷其三族,又诛杀名士何晏,后司马师又杀死夏侯玄,面对如此血腥的残杀,让草根阶层的民众和身居高位的世家大族都人人自危,唯恐成为司马家族诛杀的对象,从上到下,各阶层胆战心惊、噤若寒蝉。
而这些名士面对如此惨烈的屠杀,对统治者极度心寒,放弃参与朝政选择归隐山林,与众好友饮酒作乐、吟诗弹唱,其中不乏又个性出挑之人、行为出格知识,如饮酒狂人刘伶常狂饮不止,抬棺狂欢。而阮籍常与邻家女掌柜饮酒,醉倒之后便睡在其旁。这些行为放纵出格、有悖纲常,放到现代也是难以理解的行为,但在当时竟然在名士当中蔚然成风。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皇权凌厉对人格的极度压迫,这些名士无处抒发,在不断压抑自我的精神信仰中痛苦求生,最终放荡訾睢、无所顾忌。
此时的司马家族仍然延续以往的“九品中正制”,此制度分为家世、行状、定品三个方面,起初解决了管理选拔没有定准的问题,但到西晋,这种制度已经被世家大族所掌控,出生寒门的人行状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也能定在上品,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寒门读书人失去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只能崇尚清谈。

三、清谈的内容
所谓清谈,如何清谈?从何而谈?
清谈,一般或为两人,或为三人,或为多人组成,他们一边喝茶饮酒,一边畅所欲言,针对某个话题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而其讨论的终极问题则是关于有和无的问题。从正始清谈开始直至后世的竹林清谈,清谈在名士之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才思以及文学造诣的彰显,更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几乎成为了名士的必备技能之一。
清谈的场面也是十分激烈的,此时,这些游离于朝政之外以避朝廷锋芒的名士将自己的注意力尽皆集中于哲学问题的终极思考上,他们围绕着《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内容展开,分为宾主双方,围绕一个问题,反复探究其来龙去脉,主客双方往往是针锋相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想将对方辩倒,而到激烈之时,他们还会手舞足蹈,口吐粗言,忘乎所以。等到本场清谈结束后,若主客双方达成一致,则握手言和;若依旧各执一辞,就请第三方来为本场清谈做出总结性发言,之后则约好下次再论,直到对方心服口服为止。
当然,清谈对于文人墨客而言,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更是一种可以抒发情怀、展现自我才华的手段,通过清谈,文人们可以向其他文人展示出自己真正的才华,成为他人仰慕的存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士在清谈的过程中往往“盛饰麈尾。”所谓麈尾行状有点像树叶,类似于羽毛,但比羽毛更硬,可以直立起来,挥动麈尾会伴随清风拂面。在清谈之际,一边口若悬河,一边轻摇麈尾,可谓清雅至极。
魏晋时期,清谈成风,此时文人墨客们只需一盏清茶,一杯醇酒,就可天马行空般的喋喋不休。这时,就连女性和小孩也会参与其中,比如某一次,王献之与人谈论诗文,疲于应付,被人说的是狼狈不堪,此时躲在青帘之后的嫂子谢道韫听到,忍不住谈兴大发,接着话题,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工夫,与王献之清谈的文人们就无言以对,理屈词穷,甘拜下风。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裴遐娶了太尉王衍的第四个女儿,新婚刚满三日,几个女婿就聚集到一起谈话,当时的一些名士以及王、裴两家的族人子弟都到了。西晋著名的玄学家郭象在客座上率先于裴遐发起清谈,郭象学富五车,一开始剑拔弩张、气势逼人,前袁遐几个回合略败下风,但他却从容不迫,还是娓娓道来,议论的义理和情志都显得精深微妙。满座宾客都赞叹叫好。王衍对自己女婿不俗的表现十分满意。
在这些名士的身体力行之下,清谈之风愈演愈烈。西晋时期,曾有一次空谈的盛象,据《世说新语》记载,名士们在洛水游玩,回来的时候,尚书令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王衍说裴仆射擅长谈名理,滔滔不绝,意趣高雅;张茂先谈《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安丰谈论延陵、子房,也极为奥妙。透彻,超尘拔俗。这段记载里包含了几位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我们也可从这几句话中窥见当时的清谈所谈论的内容,其中包含了玄学名理、史书正传等广阔内容。
清谈之风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曾盛行一时,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他是文人在生存危机下对自我心灵的放逐,对后世的影响有利有弊。清谈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涌现除了一批优秀文人,如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对于哲学思想以及文化的繁荣犹是功不可没。但后世历来有人评判清谈误国,就连西晋名士王衍素来擅长于清谈,人称“口中雌黄”,在被石勒杀死之前,也发出“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的慨叹,但将误国一事尽推于清谈之上未免也有失偏颇。

有人把魏晋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礼仪之邦的古老中古在这一时期首次冲破了伦理纲常的限制,纷纷崇尚名士风流,扪虱座谈、纵情饮酒、声色犬马等一度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对象。然而其实这也是历史上文人面临的最为黑暗的一个寒冬,这些看似出格放纵的事情背后实则隐藏的是魏晋名士不堪一击的政治理想、以及惶惑不安的脆弱命途,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名士们在怀抱满腔热血却被黑暗现实冰封之后,只能寄情于无所作用的清谈。
总得说,由于清谈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属于虚无之论,仅为士大夫和文人们消遣,及显示清高的一种方式,于国于民皆是毫无意义。正所谓“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清谈就是一场自吹自话的一场讨论会罢了,其所谈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空话,若是放到实际,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好清谈,而不做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清谈呢?与现代喝酒划拳还喝茶调情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些士为什么好清谈而不做事呢。对于清谈,他们自己什么态度呢。清谈为后世留下了什么呢。清谈起源于东汉末年,当时确实是出于躲避迫害三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翻身做主人西晋开始,清谈家掌握了朝政大权热衷于营私、不问国事,清谈家对西晋灭亡负有重大责任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崛起,皇权已成为强弩之末。但是在这种政治随时面临崩盘的情况下,各地却分权而立,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
而此时曹魏政权奉行“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给出生低微的有才之士打开了一扇窗,众多寒门学子凭借文采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极大的刺激了文士们的创作。一时间,社会风气大开,文学创作获得了良好的生长土壤,文坛开始活跃起来,开创了文学创作史上的“大繁荣景象”。这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被誉为“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把柔软流动之风与坚硬强健之骨结合起来,刚柔并济,反映了建安时期的文人的创作特色,这一时期的文人怀抱着济世安民的热情,在文中抒发着自己的忧国忧民、热心朝政的意识,风格大多刚健有力、热情澎湃,如曹操的《短歌行》。而魏晋风度作为与建安风骨紧紧衔接的一个时代特色,可以看作是建安风骨的延申,却在短短百年的时间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魏晋多名士,大多洒脱率性而不拘小节,从容貌而言,大多风度翩翩,形神肃立;但行为举止而言,却是沉迷药酒、行为放荡。
当然,谈到魏晋名士无法避开的就是“清谈”之风,所谓清谈,谈什么?为何名士皆尚清谈?
一、儒家思想的崩塌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世家大族崛起。当时数的上名号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世家大族权倾朝野,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倚仗自己的权势占地为王。而地主豪强也绝对不闲着,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断进行土地兼并,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此时朝野中手握兵权的武将蠢蠢欲动,社会面临分崩离析。在稳定时期发挥管理民众作用的儒学此时显得大而无用。
中央政府积弊深重,社会时局混乱。在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此时开始摇摇欲坠,而谶纬之学在这样的乱局中也频频失效。一时间,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怀疑其真实性,对于儒学的怀疑让他们冷静下来,他们不再简单的迷信儒学的空洞说教,连同着对于从前深信不疑的谶纬之学也有了新的思考。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心灵窗口,来解决现在所处时代的实际问题,此时“玄学”应运而生。
从前的儒学讲究“三纲五常”,对于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但乱局下的社会秩序已经被完全打破,这些陈词滥调显然不再适用于乱世,这一时期的知识知识分子开始从哲学的眼光去思考社会问题,即玄学,亦称新道家。他们崇尚老子的思想,玄学的名字也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围绕着围绕《周易》、《老子》、《庄子》等玄妙深奥的话题展开辩论,称之为“清谈”(也叫“玄谈”)。当时的清谈可谓笼络天下名士,如历史上又名的谢安、王导,即是在朝高官,又是清谈高手。

二、士大夫莫谈国事
司马懿一生机关算尽,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强大汉朝最后一线荣光降落之际,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位。他的上位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街头巷尾窃窃私语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司马家族深知其中道理,所以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堵上民众地嘴。司马家族对于士族阶层采取严格的舆论控制,并且做出了具体行动,司马懿诛杀曹爽等,并夷其三族,又诛杀名士何晏,后司马师又杀死夏侯玄,面对如此血腥的残杀,让草根阶层的民众和身居高位的世家大族都人人自危,唯恐成为司马家族诛杀的对象,从上到下,各阶层胆战心惊、噤若寒蝉。
而这些名士面对如此惨烈的屠杀,对统治者极度心寒,放弃参与朝政选择归隐山林,与众好友饮酒作乐、吟诗弹唱,其中不乏又个性出挑之人、行为出格知识,如饮酒狂人刘伶常狂饮不止,抬棺狂欢。而阮籍常与邻家女掌柜饮酒,醉倒之后便睡在其旁。这些行为放纵出格、有悖纲常,放到现代也是难以理解的行为,但在当时竟然在名士当中蔚然成风。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皇权凌厉对人格的极度压迫,这些名士无处抒发,在不断压抑自我的精神信仰中痛苦求生,最终放荡訾睢、无所顾忌。
此时的司马家族仍然延续以往的“九品中正制”,此制度分为家世、行状、定品三个方面,起初解决了管理选拔没有定准的问题,但到西晋,这种制度已经被世家大族所掌控,出生寒门的人行状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也能定在上品,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寒门读书人失去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只能崇尚清谈。

三、清谈的内容
所谓清谈,如何清谈?从何而谈?
清谈,一般或为两人,或为三人,或为多人组成,他们一边喝茶饮酒,一边畅所欲言,针对某个话题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而其讨论的终极问题则是关于有和无的问题。从正始清谈开始直至后世的竹林清谈,清谈在名士之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才思以及文学造诣的彰显,更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几乎成为了名士的必备技能之一。
清谈的场面也是十分激烈的,此时,这些游离于朝政之外以避朝廷锋芒的名士将自己的注意力尽皆集中于哲学问题的终极思考上,他们围绕着《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内容展开,分为宾主双方,围绕一个问题,反复探究其来龙去脉,主客双方往往是针锋相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想将对方辩倒,而到激烈之时,他们还会手舞足蹈,口吐粗言,忘乎所以。等到本场清谈结束后,若主客双方达成一致,则握手言和;若依旧各执一辞,就请第三方来为本场清谈做出总结性发言,之后则约好下次再论,直到对方心服口服为止。
当然,清谈对于文人墨客而言,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更是一种可以抒发情怀、展现自我才华的手段,通过清谈,文人们可以向其他文人展示出自己真正的才华,成为他人仰慕的存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士在清谈的过程中往往“盛饰麈尾。”所谓麈尾行状有点像树叶,类似于羽毛,但比羽毛更硬,可以直立起来,挥动麈尾会伴随清风拂面。在清谈之际,一边口若悬河,一边轻摇麈尾,可谓清雅至极。
魏晋时期,清谈成风,此时文人墨客们只需一盏清茶,一杯醇酒,就可天马行空般的喋喋不休。这时,就连女性和小孩也会参与其中,比如某一次,王献之与人谈论诗文,疲于应付,被人说的是狼狈不堪,此时躲在青帘之后的嫂子谢道韫听到,忍不住谈兴大发,接着话题,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工夫,与王献之清谈的文人们就无言以对,理屈词穷,甘拜下风。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裴遐娶了太尉王衍的第四个女儿,新婚刚满三日,几个女婿就聚集到一起谈话,当时的一些名士以及王、裴两家的族人子弟都到了。西晋著名的玄学家郭象在客座上率先于裴遐发起清谈,郭象学富五车,一开始剑拔弩张、气势逼人,前袁遐几个回合略败下风,但他却从容不迫,还是娓娓道来,议论的义理和情志都显得精深微妙。满座宾客都赞叹叫好。王衍对自己女婿不俗的表现十分满意。
在这些名士的身体力行之下,清谈之风愈演愈烈。西晋时期,曾有一次空谈的盛象,据《世说新语》记载,名士们在洛水游玩,回来的时候,尚书令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王衍说裴仆射擅长谈名理,滔滔不绝,意趣高雅;张茂先谈《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安丰谈论延陵、子房,也极为奥妙。透彻,超尘拔俗。这段记载里包含了几位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我们也可从这几句话中窥见当时的清谈所谈论的内容,其中包含了玄学名理、史书正传等广阔内容。
清谈之风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曾盛行一时,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他是文人在生存危机下对自我心灵的放逐,对后世的影响有利有弊。清谈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涌现除了一批优秀文人,如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对于哲学思想以及文化的繁荣犹是功不可没。但后世历来有人评判清谈误国,就连西晋名士王衍素来擅长于清谈,人称“口中雌黄”,在被石勒杀死之前,也发出“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的慨叹,但将误国一事尽推于清谈之上未免也有失偏颇。

有人把魏晋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礼仪之邦的古老中古在这一时期首次冲破了伦理纲常的限制,纷纷崇尚名士风流,扪虱座谈、纵情饮酒、声色犬马等一度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对象。然而其实这也是历史上文人面临的最为黑暗的一个寒冬,这些看似出格放纵的事情背后实则隐藏的是魏晋名士不堪一击的政治理想、以及惶惑不安的脆弱命途,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名士们在怀抱满腔热血却被黑暗现实冰封之后,只能寄情于无所作用的清谈。
总得说,由于清谈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属于虚无之论,仅为士大夫和文人们消遣,及显示清高的一种方式,于国于民皆是毫无意义。正所谓“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清谈就是一场自吹自话的一场讨论会罢了,其所谈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空话,若是放到实际,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好清谈,而不做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清谈呢?与现代喝酒划拳还喝茶调情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些士为什么好清谈而不做事呢。对于清谈,他们自己什么态度呢。清谈为后世留下了什么呢。清谈起源于东汉末年,当时确实是出于躲避迫害三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翻身做主人西晋开始,清谈家掌握了朝政大权热衷于营私、不问国事,清谈家对西晋灭亡负有重大责任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崛起,皇权已成为强弩之末。但是在这种政治随时面临崩盘的情况下,各地却分权而立,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
而此时曹魏政权奉行“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给出生低微的有才之士打开了一扇窗,众多寒门学子凭借文采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极大的刺激了文士们的创作。一时间,社会风气大开,文学创作获得了良好的生长土壤,文坛开始活跃起来,开创了文学创作史上的“大繁荣景象”。这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被誉为“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把柔软流动之风与坚硬强健之骨结合起来,刚柔并济,反映了建安时期的文人的创作特色,这一时期的文人怀抱着济世安民的热情,在文中抒发着自己的忧国忧民、热心朝政的意识,风格大多刚健有力、热情澎湃,如曹操的《短歌行》。而魏晋风度作为与建安风骨紧紧衔接的一个时代特色,可以看作是建安风骨的延申,却在短短百年的时间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魏晋多名士,大多洒脱率性而不拘小节,从容貌而言,大多风度翩翩,形神肃立;但行为举止而言,却是沉迷药酒、行为放荡。
当然,谈到魏晋名士无法避开的就是“清谈”之风,所谓清谈,谈什么?为何名士皆尚清谈?
一、儒家思想的崩塌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世家大族崛起。当时数的上名号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世家大族权倾朝野,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倚仗自己的权势占地为王。而地主豪强也绝对不闲着,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断进行土地兼并,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此时朝野中手握兵权的武将蠢蠢欲动,社会面临分崩离析。在稳定时期发挥管理民众作用的儒学此时显得大而无用。
中央政府积弊深重,社会时局混乱。在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此时开始摇摇欲坠,而谶纬之学在这样的乱局中也频频失效。一时间,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怀疑其真实性,对于儒学的怀疑让他们冷静下来,他们不再简单的迷信儒学的空洞说教,连同着对于从前深信不疑的谶纬之学也有了新的思考。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心灵窗口,来解决现在所处时代的实际问题,此时“玄学”应运而生。
从前的儒学讲究“三纲五常”,对于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但乱局下的社会秩序已经被完全打破,这些陈词滥调显然不再适用于乱世,这一时期的知识知识分子开始从哲学的眼光去思考社会问题,即玄学,亦称新道家。他们崇尚老子的思想,玄学的名字也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围绕着围绕《周易》、《老子》、《庄子》等玄妙深奥的话题展开辩论,称之为“清谈”(也叫“玄谈”)。当时的清谈可谓笼络天下名士,如历史上又名的谢安、王导,即是在朝高官,又是清谈高手。

二、士大夫莫谈国事
司马懿一生机关算尽,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强大汉朝最后一线荣光降落之际,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位。他的上位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街头巷尾窃窃私语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司马家族深知其中道理,所以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堵上民众地嘴。司马家族对于士族阶层采取严格的舆论控制,并且做出了具体行动,司马懿诛杀曹爽等,并夷其三族,又诛杀名士何晏,后司马师又杀死夏侯玄,面对如此血腥的残杀,让草根阶层的民众和身居高位的世家大族都人人自危,唯恐成为司马家族诛杀的对象,从上到下,各阶层胆战心惊、噤若寒蝉。
而这些名士面对如此惨烈的屠杀,对统治者极度心寒,放弃参与朝政选择归隐山林,与众好友饮酒作乐、吟诗弹唱,其中不乏又个性出挑之人、行为出格知识,如饮酒狂人刘伶常狂饮不止,抬棺狂欢。而阮籍常与邻家女掌柜饮酒,醉倒之后便睡在其旁。这些行为放纵出格、有悖纲常,放到现代也是难以理解的行为,但在当时竟然在名士当中蔚然成风。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皇权凌厉对人格的极度压迫,这些名士无处抒发,在不断压抑自我的精神信仰中痛苦求生,最终放荡訾睢、无所顾忌。
此时的司马家族仍然延续以往的“九品中正制”,此制度分为家世、行状、定品三个方面,起初解决了管理选拔没有定准的问题,但到西晋,这种制度已经被世家大族所掌控,出生寒门的人行状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也能定在上品,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寒门读书人失去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只能崇尚清谈。

三、清谈的内容
所谓清谈,如何清谈?从何而谈?
清谈,一般或为两人,或为三人,或为多人组成,他们一边喝茶饮酒,一边畅所欲言,针对某个话题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而其讨论的终极问题则是关于有和无的问题。从正始清谈开始直至后世的竹林清谈,清谈在名士之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才思以及文学造诣的彰显,更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几乎成为了名士的必备技能之一。
清谈的场面也是十分激烈的,此时,这些游离于朝政之外以避朝廷锋芒的名士将自己的注意力尽皆集中于哲学问题的终极思考上,他们围绕着《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内容展开,分为宾主双方,围绕一个问题,反复探究其来龙去脉,主客双方往往是针锋相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想将对方辩倒,而到激烈之时,他们还会手舞足蹈,口吐粗言,忘乎所以。等到本场清谈结束后,若主客双方达成一致,则握手言和;若依旧各执一辞,就请第三方来为本场清谈做出总结性发言,之后则约好下次再论,直到对方心服口服为止。
当然,清谈对于文人墨客而言,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更是一种可以抒发情怀、展现自我才华的手段,通过清谈,文人们可以向其他文人展示出自己真正的才华,成为他人仰慕的存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士在清谈的过程中往往“盛饰麈尾。”所谓麈尾行状有点像树叶,类似于羽毛,但比羽毛更硬,可以直立起来,挥动麈尾会伴随清风拂面。在清谈之际,一边口若悬河,一边轻摇麈尾,可谓清雅至极。
魏晋时期,清谈成风,此时文人墨客们只需一盏清茶,一杯醇酒,就可天马行空般的喋喋不休。这时,就连女性和小孩也会参与其中,比如某一次,王献之与人谈论诗文,疲于应付,被人说的是狼狈不堪,此时躲在青帘之后的嫂子谢道韫听到,忍不住谈兴大发,接着话题,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工夫,与王献之清谈的文人们就无言以对,理屈词穷,甘拜下风。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裴遐娶了太尉王衍的第四个女儿,新婚刚满三日,几个女婿就聚集到一起谈话,当时的一些名士以及王、裴两家的族人子弟都到了。西晋著名的玄学家郭象在客座上率先于裴遐发起清谈,郭象学富五车,一开始剑拔弩张、气势逼人,前袁遐几个回合略败下风,但他却从容不迫,还是娓娓道来,议论的义理和情志都显得精深微妙。满座宾客都赞叹叫好。王衍对自己女婿不俗的表现十分满意。
在这些名士的身体力行之下,清谈之风愈演愈烈。西晋时期,曾有一次空谈的盛象,据《世说新语》记载,名士们在洛水游玩,回来的时候,尚书令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王衍说裴仆射擅长谈名理,滔滔不绝,意趣高雅;张茂先谈《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安丰谈论延陵、子房,也极为奥妙。透彻,超尘拔俗。这段记载里包含了几位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我们也可从这几句话中窥见当时的清谈所谈论的内容,其中包含了玄学名理、史书正传等广阔内容。
清谈之风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曾盛行一时,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他是文人在生存危机下对自我心灵的放逐,对后世的影响有利有弊。清谈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涌现除了一批优秀文人,如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对于哲学思想以及文化的繁荣犹是功不可没。但后世历来有人评判清谈误国,就连西晋名士王衍素来擅长于清谈,人称“口中雌黄”,在被石勒杀死之前,也发出“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的慨叹,但将误国一事尽推于清谈之上未免也有失偏颇。

有人把魏晋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礼仪之邦的古老中古在这一时期首次冲破了伦理纲常的限制,纷纷崇尚名士风流,扪虱座谈、纵情饮酒、声色犬马等一度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对象。然而其实这也是历史上文人面临的最为黑暗的一个寒冬,这些看似出格放纵的事情背后实则隐藏的是魏晋名士不堪一击的政治理想、以及惶惑不安的脆弱命途,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名士们在怀抱满腔热血却被黑暗现实冰封之后,只能寄情于无所作用的清谈。
总得说,由于清谈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属于虚无之论,仅为士大夫和文人们消遣,及显示清高的一种方式,于国于民皆是毫无意义。正所谓“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清谈就是一场自吹自话的一场讨论会罢了,其所谈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空话,若是放到实际,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好清谈,而不做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清谈呢?与现代喝酒划拳还喝茶调情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些士为什么好清谈而不做事呢。对于清谈,他们自己什么态度呢。清谈为后世留下了什么呢。清谈起源于东汉末年,当时确实是出于躲避迫害三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翻身做主人西晋开始,清谈家掌握了朝政大权热衷于营私、不问国事,清谈家对西晋灭亡负有重大责任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崛起,皇权已成为强弩之末。但是在这种政治随时面临崩盘的情况下,各地却分权而立,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
而此时曹魏政权奉行“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给出生低微的有才之士打开了一扇窗,众多寒门学子凭借文采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极大的刺激了文士们的创作。一时间,社会风气大开,文学创作获得了良好的生长土壤,文坛开始活跃起来,开创了文学创作史上的“大繁荣景象”。这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被誉为“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把柔软流动之风与坚硬强健之骨结合起来,刚柔并济,反映了建安时期的文人的创作特色,这一时期的文人怀抱着济世安民的热情,在文中抒发着自己的忧国忧民、热心朝政的意识,风格大多刚健有力、热情澎湃,如曹操的《短歌行》。而魏晋风度作为与建安风骨紧紧衔接的一个时代特色,可以看作是建安风骨的延申,却在短短百年的时间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魏晋多名士,大多洒脱率性而不拘小节,从容貌而言,大多风度翩翩,形神肃立;但行为举止而言,却是沉迷药酒、行为放荡。
当然,谈到魏晋名士无法避开的就是“清谈”之风,所谓清谈,谈什么?为何名士皆尚清谈?
一、儒家思想的崩塌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世家大族崛起。当时数的上名号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世家大族权倾朝野,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倚仗自己的权势占地为王。而地主豪强也绝对不闲着,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断进行土地兼并,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此时朝野中手握兵权的武将蠢蠢欲动,社会面临分崩离析。在稳定时期发挥管理民众作用的儒学此时显得大而无用。
中央政府积弊深重,社会时局混乱。在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此时开始摇摇欲坠,而谶纬之学在这样的乱局中也频频失效。一时间,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怀疑其真实性,对于儒学的怀疑让他们冷静下来,他们不再简单的迷信儒学的空洞说教,连同着对于从前深信不疑的谶纬之学也有了新的思考。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心灵窗口,来解决现在所处时代的实际问题,此时“玄学”应运而生。
从前的儒学讲究“三纲五常”,对于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但乱局下的社会秩序已经被完全打破,这些陈词滥调显然不再适用于乱世,这一时期的知识知识分子开始从哲学的眼光去思考社会问题,即玄学,亦称新道家。他们崇尚老子的思想,玄学的名字也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围绕着围绕《周易》、《老子》、《庄子》等玄妙深奥的话题展开辩论,称之为“清谈”(也叫“玄谈”)。当时的清谈可谓笼络天下名士,如历史上又名的谢安、王导,即是在朝高官,又是清谈高手。

二、士大夫莫谈国事
司马懿一生机关算尽,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强大汉朝最后一线荣光降落之际,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位。他的上位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街头巷尾窃窃私语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司马家族深知其中道理,所以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堵上民众地嘴。司马家族对于士族阶层采取严格的舆论控制,并且做出了具体行动,司马懿诛杀曹爽等,并夷其三族,又诛杀名士何晏,后司马师又杀死夏侯玄,面对如此血腥的残杀,让草根阶层的民众和身居高位的世家大族都人人自危,唯恐成为司马家族诛杀的对象,从上到下,各阶层胆战心惊、噤若寒蝉。
而这些名士面对如此惨烈的屠杀,对统治者极度心寒,放弃参与朝政选择归隐山林,与众好友饮酒作乐、吟诗弹唱,其中不乏又个性出挑之人、行为出格知识,如饮酒狂人刘伶常狂饮不止,抬棺狂欢。而阮籍常与邻家女掌柜饮酒,醉倒之后便睡在其旁。这些行为放纵出格、有悖纲常,放到现代也是难以理解的行为,但在当时竟然在名士当中蔚然成风。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皇权凌厉对人格的极度压迫,这些名士无处抒发,在不断压抑自我的精神信仰中痛苦求生,最终放荡訾睢、无所顾忌。
此时的司马家族仍然延续以往的“九品中正制”,此制度分为家世、行状、定品三个方面,起初解决了管理选拔没有定准的问题,但到西晋,这种制度已经被世家大族所掌控,出生寒门的人行状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也能定在上品,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寒门读书人失去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只能崇尚清谈。

三、清谈的内容
所谓清谈,如何清谈?从何而谈?
清谈,一般或为两人,或为三人,或为多人组成,他们一边喝茶饮酒,一边畅所欲言,针对某个话题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而其讨论的终极问题则是关于有和无的问题。从正始清谈开始直至后世的竹林清谈,清谈在名士之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不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才思以及文学造诣的彰显,更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几乎成为了名士的必备技能之一。
清谈的场面也是十分激烈的,此时,这些游离于朝政之外以避朝廷锋芒的名士将自己的注意力尽皆集中于哲学问题的终极思考上,他们围绕着《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内容展开,分为宾主双方,围绕一个问题,反复探究其来龙去脉,主客双方往往是针锋相对,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想将对方辩倒,而到激烈之时,他们还会手舞足蹈,口吐粗言,忘乎所以。等到本场清谈结束后,若主客双方达成一致,则握手言和;若依旧各执一辞,就请第三方来为本场清谈做出总结性发言,之后则约好下次再论,直到对方心服口服为止。
当然,清谈对于文人墨客而言,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更是一种可以抒发情怀、展现自我才华的手段,通过清谈,文人们可以向其他文人展示出自己真正的才华,成为他人仰慕的存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士在清谈的过程中往往“盛饰麈尾。”所谓麈尾行状有点像树叶,类似于羽毛,但比羽毛更硬,可以直立起来,挥动麈尾会伴随清风拂面。在清谈之际,一边口若悬河,一边轻摇麈尾,可谓清雅至极。
魏晋时期,清谈成风,此时文人墨客们只需一盏清茶,一杯醇酒,就可天马行空般的喋喋不休。这时,就连女性和小孩也会参与其中,比如某一次,王献之与人谈论诗文,疲于应付,被人说的是狼狈不堪,此时躲在青帘之后的嫂子谢道韫听到,忍不住谈兴大发,接着话题,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工夫,与王献之清谈的文人们就无言以对,理屈词穷,甘拜下风。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裴遐娶了太尉王衍的第四个女儿,新婚刚满三日,几个女婿就聚集到一起谈话,当时的一些名士以及王、裴两家的族人子弟都到了。西晋著名的玄学家郭象在客座上率先于裴遐发起清谈,郭象学富五车,一开始剑拔弩张、气势逼人,前袁遐几个回合略败下风,但他却从容不迫,还是娓娓道来,议论的义理和情志都显得精深微妙。满座宾客都赞叹叫好。王衍对自己女婿不俗的表现十分满意。
在这些名士的身体力行之下,清谈之风愈演愈烈。西晋时期,曾有一次空谈的盛象,据《世说新语》记载,名士们在洛水游玩,回来的时候,尚书令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王衍说裴仆射擅长谈名理,滔滔不绝,意趣高雅;张茂先谈《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安丰谈论延陵、子房,也极为奥妙。透彻,超尘拔俗。这段记载里包含了几位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我们也可从这几句话中窥见当时的清谈所谈论的内容,其中包含了玄学名理、史书正传等广阔内容。
清谈之风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曾盛行一时,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他是文人在生存危机下对自我心灵的放逐,对后世的影响有利有弊。清谈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涌现除了一批优秀文人,如竹林七贤、正始名士等,对于哲学思想以及文化的繁荣犹是功不可没。但后世历来有人评判清谈误国,就连西晋名士王衍素来擅长于清谈,人称“口中雌黄”,在被石勒杀死之前,也发出“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的慨叹,但将误国一事尽推于清谈之上未免也有失偏颇。

有人把魏晋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礼仪之邦的古老中古在这一时期首次冲破了伦理纲常的限制,纷纷崇尚名士风流,扪虱座谈、纵情饮酒、声色犬马等一度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对象。然而其实这也是历史上文人面临的最为黑暗的一个寒冬,这些看似出格放纵的事情背后实则隐藏的是魏晋名士不堪一击的政治理想、以及惶惑不安的脆弱命途,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名士们在怀抱满腔热血却被黑暗现实冰封之后,只能寄情于无所作用的清谈。
总得说,由于清谈是从玄学发展而来,属于虚无之论,仅为士大夫和文人们消遣,及显示清高的一种方式,于国于民皆是毫无意义。正所谓“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清谈就是一场自吹自话的一场讨论会罢了,其所谈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空话,若是放到实际,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朗读本文
朗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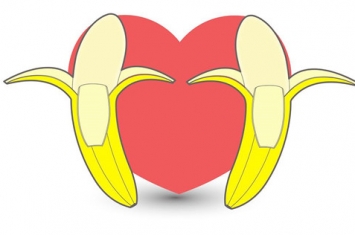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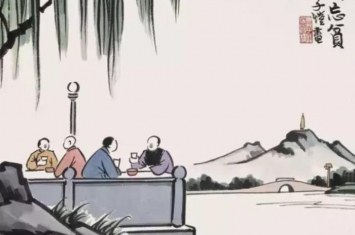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