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写一篇蛇的文章,关于蛇的灵性,关于父亲灵魂的寄托,以及关于所谓的灵异。
我是那种看到蛇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人。
人生中第一次惊悚于蛇的,是小时候的一个春天里,在粉粉的白色槐花怒放,香味溢满河岸的芦苇丛中打粽叶,打着打着,抬头看天,会蓦然发现高大的槐树上,一条灰色长蛇像根扁担一样,舒展着身子趴在枝头上,你望它的时候,它也正望着你,无论从哪个角度去仰视它,它都是趾高气昂地盯着你。

在农村,看见蛇不奇怪,尤其是春夏秋季。但蛇在冬天出现就见怪而怪了。
定义蛇有灵性,其实是始于父亲从生病前,到离开后,经常会有跟蛇有关的故事出现,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某种约定,但从此我对蛇有了特殊的情感。
父亲2000年的正月里因为吞咽不畅,去医院检查发现食道癌中晚期。而上一年冬天里,父亲曾经跟母亲说过,他清晨去屋外蹲茅厕,在茅坑里看见过蛇,红色的,不止一次。冬天的季节,蛇本应该冬眠于地下,严寒的天却暴露在父亲眼皮地下几次,似乎在暗示着某种不详的预兆。更奇怪的是,只有父亲看见过,其他人都没遇到这样的情形。
从发现病情到去世,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年头到年尾,父亲就这样从活生生的肉身变成白灰。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夏天,我将母亲接城里来和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初秋农村收获的季节,我送母亲回去。坐长途车再辗转短途车到家,离老宅还有几步远的地方,看到一条菜色小蛇骨碌碌在地上扑面游来,好像认识路似的,拐弯直接去了还锁着的屋门,母亲连忙拿钥匙打开门,进屋里找。正好邻居大叔路过,喊他帮忙,最后在囤粮食的旮旯里发现它蜷曲着不动,母亲拿个挖地的大铁锹给大叔,大叔将小蛇铲起来沿着它游来的方向,送出去很远,可它还是原方向游来,母亲即跟它说话:你再游回来就打死你。小蛇好像听懂人话,掉头游去。母亲当时喃喃自语:会不会你爸变的,知道我们回来了。我也默认是,因为时间上卡的很凑巧。

后来的两三年里,母亲提过几次关于蛇的出现,都是我在电话里听来的:有次夏天,她中午没吃饭还去地里干活,半路上,从庄家丛中游出来一条大蛇横在她前面,她吓的转身回家。她问我:会不会是你爸拦着不让去地里干活?我开玩笑道:天热,蛇出来找水喝的吧。不过,父亲在世时确实都是十一点半准时吃饭,不让去地里的。还有次,秋天,她在门口晒粮食,无意中转过头一看,一条蛇在她身边的粮食堆上趴着,又把她吓一大跳,她跟蛇说,赶紧走,再不走就打咯,蛇好像听懂人话,真就游走了。
我有个远房堂伯,一辈子无儿无女,村里人都称其为绝后代。堂伯活到93岁,咽气那天的傍晚,二哥家院子里爬出来一条大蟒蛇,盘成八卦,张开大口,像要吃人。堂伯的父亲和我父亲的父亲是亲兄弟,堂伯离开那天是个早晨,按照风俗,母亲和大哥二哥听到消息就要第一时间去送纸磕头,可那天他们直到蟒蛇出现也还没去,母亲后来电话里跟我说:会不会又是你爸变成蛇发火,嫌去送纸送迟了?
几次蛇的出现,对于母亲的臆测,我诠释为:父亲虽然离开这么多年,但依然活在她的心中,宁可信其有那是父亲变成的蛇,也算活着的人对已经离开人的一种深深的精神寄托吧。
我自己对一些不能用科学常识解释的奇怪现象,或者认为灵异,也会倾向于用父亲的灵魂做掩护,而去宁愿相信父亲虽然肉体不存在,但心灵感应或者说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缥缈时刻伴随身边,就当他一直在高处,在我们看不见他,而他却看得见我们的不远处,望着我们关心着我们,如同小时候看到大树上横趴着的那条蛇静静地俯视一样,仅仅只可以看着。
蛇的灵性,我希望它真的有,有寄予的心灵托付,不失为给活着人对已故亲人的一种念想,而有念想,才更有希望生活好。

灵魂的有无,我无法证实,但我对几年前一个冬天,在母亲家吃晚饭亲历的事情耿耿不能释怀,说给任何人听,肯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解释,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于别人更是不会清楚。
那是个晚饭的时辰,一家人坐桌上津津有味地吃着。母亲的屋子有前后门,大冷天都关的严严实实, 可以百分百地确定没有一丝风。边吃边谈家常中,我右手拿着的一双筷子在我低头刹那间,发现一条非常完整的蜈蚣壳躺在我夹菜那头的两根筷子上,不偏不倚的角度,恰到好处地沿着筷子方向横在筷头上,就算是刻意抓个放上去也没那么位置正,因为那样的脊椎动物脱出来的皮是很轻很轻的。我随即让坐旁边的姐姐也看了一眼,她什么也没没说。当时倒没深究太多,只把筷子抖了抖,那条蜈蚣壳掉桌上后就继续吃饭,后来想着想着不对劲,在不多的残羹里去找它,却怎么也没找着。
事后,我曾分析过:首先没有风吹,如果说,母亲房子头顶屋檐上有蜈蚣脱的壳,在不管什么力量的冲击下掉下来,怎么掉也不会不偏不倚正好掉出那个角度;其次,即使飘着下来,那么长的壳子在落下的过程里,有日光灯的照耀,怎么着也会被桌上的其他人看到,可它偏偏于无形神秘中突然出现,而且就落在我拿着的筷子上,如同一根菜在被抬着即将要放入嘴里。逻辑上是没有理由的。

如果不能用所学知识去化解我所见的,那么我想到的也是和母亲一样的思维:父亲的灵魂再次出现,他用他的化身和我玩个游戏罢了。好比看神话剧里,仙人指路,手臂一挥,荆棘丛中劈开一条生死路;或者口念阿弥陀佛,手指头一点,危难之时,嗖一声,如入无人之境,穿墙而过。
这篇文章出来后,我不知道读到的人会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不管是什么,我只可以保证的是:这都是我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的。我虽然害怕看到蛇,但对蛇怀有敬畏和奇特的爱惜,就因为它在父亲生前生后出现过多次。



 朗读本文
朗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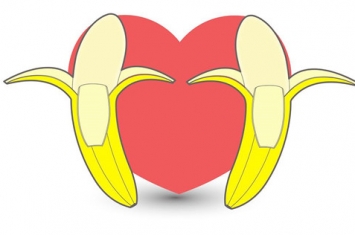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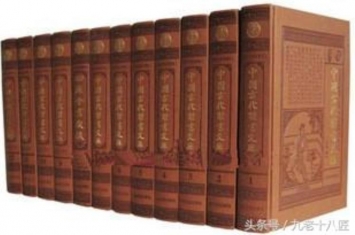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