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上一世纪20年代周仁先生率先研究古陶瓷算起,那么,我国陶瓷科技考古已有了80年的发展史。1998年,李家治先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集数十年成果之大成,构建起中国古陶瓷科技发展的体系,使中国古陶瓷科技考古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近10年来,陶瓷科技考古的研究工作依然处于上升趋势。2000年始,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方向性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的资助下,我们将陶器产地研究拓宽至瓷器工艺和产地的研究。研究中,我们在充分尊重前人成果的同时,发扬勇于创新之精神。这样,既迅速切入到古陶瓷研究的前沿领域,又不断产生并完善着新的研究思路。

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中,原始瓷产地研究之进展,涉及中国古陶瓷科技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受其启示,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路,现将其简要介绍如下,以期引起有关专家的关注和讨论。
人们知道,原始瓷产地研究历来有两种观点。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原始瓷发源于南方,且主要为江西的吴城地区。其理由大约有三点,一是中国北方商周时期未发现烧制原始瓷的高温窑,二是北方盛产高岭土,但不产瓷土,即缺乏烧制原始瓷的原料,三是聚类分析方面的证据。有工作指出,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江西吴城出土的原始瓷与江西吴城的出土陶器聚在一起,既然陶器原料系就地选择,那么,似乎可以推测上述地区出土的原始瓷皆产于江西吴城地区。
然而,认真推敲,前两点理由或与事实不符,或颇牵强附会,都不能一锤定音。要知道,虽然商周时期中国北方确实未发现烧制原始瓷的高温窑,但未发现不等于不存在。正如中国南方除大溪文化等地区外,尽管所发现的早期窑炉皆为龙窑,但人们并不能以此推断在龙窑之前,没有横穴窑或竖穴窑的发展阶段,个中的道理是相同的。
而矿藏资料表明,中国北方不少地方都发现有瓷土矿,如河北白错后沟、山东淄博、河南巩义、黑龙江讷河县和宝清县等地。且最近二里头二期出土白陶的分析数据也指出,其原料确为瓷土矿。至于上述聚类分析的工作,因将原始瓷和陶器的原料混为一谈,故同样不足为据。
少数学者发现,中国北方出土的商周时期原始瓷中,相当一部分为中原风格器型,且有不少烧流的残品,据此指出,这部分原始瓷应该产于我国北方。按理讲,这两个事实,特别是后一个事实,完全可确凿无疑地断定商周时期我国北方也产原始瓷。然而,或许无缘目睹这批烧流的残品,或许认为这里缺少分析数据,总之,持异议者皆未正面解答这一烧流残品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一现实,引发起重新探索原始瓷产地之兴趣。无疑,重新探索需认真调研前人的工作。
统计分析已有数据不难发现,中国南方出土的原始瓷数量确实远多于北方,但商代早期的原始瓷数量,却是北方略多于南方。不仅如此,若将吴城和中国北方商代早期的原始瓷样品做一对比分析,吴城原始瓷的质量甚差,而北方的质量颇佳,这些不争的事实显然有利于中国北方商代早期也产原始瓷的观点,从而对原始瓷的产地问题重新作一探索。
于是,分别从江西吴城、浙江黄梅山、安徽枞阳汤家墩、郑州商城和垣曲商城遗址选取了数十枚原始瓷残片样品,采用ICP和XRF等方法,测定它们的微量元素,再将这批数据作聚类和主因子分析,其结果显示,垣曲商城的原始瓷自成一类。
郑州商城的两枚原始瓷残片虽然分别归入吴城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小类内,但在稀土特征参数值的聚类分析中,郑州商城的原始瓷还是独自聚成了一类。显然,这些结果有利于商周时期我国北方也产原始瓷的观点。值得指出的是,前些年二里头二期发现的一批原始瓷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将中国原始瓷的起源向前提至夏代,而且也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北方也产原始瓷的见解。
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北方商周时期也产原始瓷的现实,迫使人们重新检验整个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史。首先,既然我国北方原始瓷的起源不晚于南方,那么,它势必直接推动北方瓷器的发展。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似乎认为,自秦汉至北朝,我国北方除烧制一些绿釉、黄釉等陶器外,基本没有瓷器的生产。即便出土了原始瓷或青瓷,也总是将其判断为来自南方的“舶来品”。
尽管这种解释十分简单明了,但颇为主观武断,实难令人信服。实际上,至少在北朝,安阳地区的相州窑已烧制成瓷釉接近白色的青瓷,那时,因北齐皇帝和民间皆崇尚白色,人们有了明确追求,通过在瓷坯上施化妆土或胎料精选,使原已较白的青瓷迅速演变为最初的白瓷。
显然,无论白瓷,还是这种瓷釉接近白色的青瓷,皆要求较高的制作工艺,而这种制作工艺必然有一个发展过程。联想到北方夏商周时期也产原始瓷的事实,中国北方早期瓷器应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认真探索这一发展过程,很可能成为今后中国陶瓷科技考古和古陶瓷科技发展史的研究热点之一。
其次,研究原始瓷,必然涉及到原始瓷与青瓷的关系问题。应该承认,将早期瓷器划分为原始瓷和青瓷两个发展阶段,即瓷器的不甚成熟阶段和成熟阶段,曾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古陶瓷研究的进展。然而,由于未能从原料配方或烧成工艺角度明确原始瓷与青瓷的本质差异,于是,随着考古发掘新成果的大量涌现和有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两者的界线似乎又模糊起来。



 朗读本文
朗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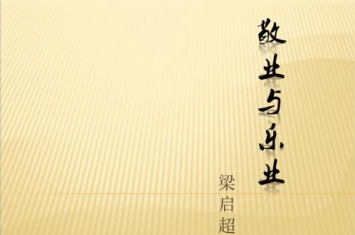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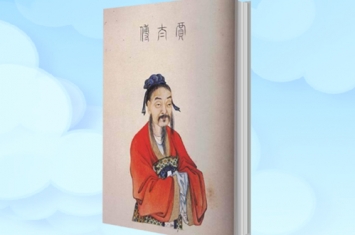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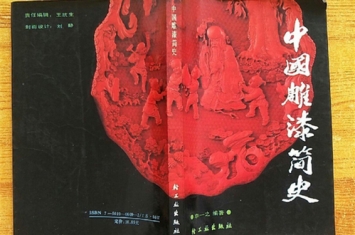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