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尽心下》中有这么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里的“书”,指的是《尚书》,《武成》则是《尚书》中的一章,所以这句话的本意是“如果完全相信《尚书》,那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武成》这一章,只取其中的两三个竹简。”《尚书》,是一本史书,而《武成》的内容则是关于武王伐纣,血流浮杵。
这句话也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大部分史书,道理很简单,一来人力有时而穷,史书的编写者无论多么用心,由于种种原因,难免还是会出现疏漏。

其次则是后人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得本来无错的内容出现错误。有意的修改自不必细说,古往今来并不少见,而无意的修改也同样不少,譬如开篇提到的那一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现在这一句的意思完全是教导孩子们不能全信书本。和原意相去甚远,但这并未有意为之,仅仅是流传过程中的自然流变。
那么,书回正题,既然史书很难没有差错,号称是史界离骚的大名鼎鼎的《史记》,又有没有错漏呢?这当然是有的,《史记》被篡改的内容不少,而且,由于秦朝本身信奉法家,和儒家结怨甚深,所以有关秦朝的历史,更是被篡改的重灾区。
譬如说李斯和二世的死,书中记载简直称得上一句离奇曲折,尤其李斯之死,更是有明显的前后矛盾,实在难以信服。而关于“指鹿为马”一事,其发生时间更是奇怪,此时秦二世应该已经被杀了,又何来“指鹿为马”呢?这些脱漏之处,我将在下文中一一叙述。
一、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一事在《史记》多有提及,无论是《秦始皇本纪》或者《李斯列传》中,都有记载,这本身即有刻意之嫌,“指鹿为马”只是一件小事,而非事关天下的军国大事,又何必分别在两处记载呢?
而在《秦始皇本纪》中,当先一句“八月已亥,赵高欲为乱”。这一句更是奇怪,秦汉史料的搜集流传非常困难,能指出具体月份的更是少之又少,而能精准到日的,几乎无一例外全是震动天下的军国大事,试问,“指鹿为马”这一件小事何德何能与这些事并列呢?
而翻阅《秦本纪》还有更加奇怪的事情,秦朝诸位皇帝,从孝文之后,每位皇帝的祭日都有记载,唯独少了秦二世。
“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十二年....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九月辛丑,葬”。那么,秦二世是什么时候驾崩的呢?在《秦楚之际月表中》有记载,是“二世三年八月,赵高杀二世”。
指鹿为马是什么时候呢?是二世三年八月已亥,这两件事是同一月发生的,请问,赵高何必要在杀二世的前十天,用这么一个愚蠢的办法试探群臣呢?但假定“指鹿为马”一事为后人故意篡改而来,那么反而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八月已亥”之后原本并非是所谓的赵高指鹿为马,而是“赵高杀二世”。也正因如此,《秦本纪》中才会唯独缺少了秦二世的祭日。
二、邯郸献姬
吕不韦“以吕易嬴”有伪,已是学界定论,众多学者都论证过吕不韦所献赵姬是否已有身孕,也就是始皇究竟是否出自吕门上。其实邯郸献姬本身有着更明显的脱漏之处,首先我们看一下原文“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子楚向吕不韦索要赵姬,吕不韦略有犹豫随即就将赵姬送出,可见赵姬身份之低下。但继续向下看,“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在这里,赵姬摇身一变,又成了赵国的豪家女,试问,赵家这种敢于对抗赵国的家族,其宗女又怎么会沦为吕不韦的姬妾,被转送犹如货物呢?
清代钱大昕所做的《二十二史考异》中就发现了这个矛盾,并提出了一种解释“盖不韦资助之,遂为邯郸豪家”。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吕不韦本身也只不过是个略有家资的商人罢了,世家豪家,吕不韦巴结都来不及,怎么能在挥手间造就一个豪强呢?
因此,赵姬被如同货物般转送和赵姬是赵豪家女两条记载,是前后矛盾的,司马迁写史的基本逻辑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为了上下文的逻辑自治,他甚至可以自行修改史实,例如将为燕谋齐的主角由苏秦改为苏代。因此,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绝非司马迁本人手笔,是很明显的后人篡改。可能的篡改者太多,例如被秦始皇强行迁移的世家豪强估计抹黑,又或者吕后执政时期的吕家自证高贵,是秦皇之后。
三、尉缭评秦王
“秦王为人,峰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这是秦汉史料中极为稀少的关于秦始皇相貌及性格的直观描写,也因此,成为了各个学者引用的高频语句。同时,这也是史记中唯一一次记载尉缭。我们今人研究史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孤证不举,因此,史记中仅仅记载一次尉缭在我们眼中就显得很突兀。在深入的研究之后,发现这其中确实有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在于“时间”,今本《尉缭子》开头即有记载“梁惠王问尉缭子”。按照《史记·六国年表》中记载,梁惠王死于公元前335年,而上面这段评价的时间是始皇十年,也就是公元前237年。前后相距82年之久,除非尉缭能活个130往上,他才能轻易的纵贯梁惠王和秦始皇两段人主。
由于之前我们一直认为今本《尉缭子》是伪作,因此对这个问题不做讨论,但近年来在银雀山汉墓中出土《尉缭子》,其内容与今本相同,排除了《尉缭子》为伪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尉缭子》与《史记》关于尉缭的记载,必有一假。研究《尉缭子》的内容,可见其内容多有吴起等战国时人,因此尉缭其实是梁惠王时人的可能性更大。
而《史记》全篇仅记载尉缭一次,也十分可疑。虽然不能确定,但这段记载是后人为故意抹黑秦皇的概率较大,也就是后人篡改《史记》之内容,其实本无此记载。至于原因,非常简单,无论是汉朝统治者还是讨厌法家和始皇的儒生,都有足够的理由来做这件事。
对于《史记》已在学界被确切指出的错漏,还有很多,但碍于篇章,再次不多赘述,对于秦汉史的研究而言,《史记》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有关秦朝的史料非常匮乏,因此,对于秦朝的研究,《史记》几乎是最主要的研究文本。
但由于汉朝政府以及后人有意的窜改,其脱漏窜乱也十分严重,班固的《汉书》中就指出,司马迁的《史记》有“十篇缺”。裴骃《史记集解序》也说过“考校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关于《史记》的考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的重重矛盾和诸多疑点,还等待学界能给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朗读本文
朗读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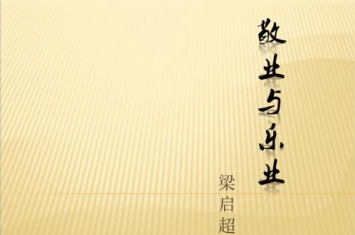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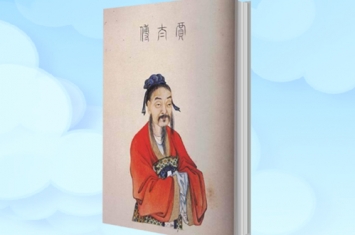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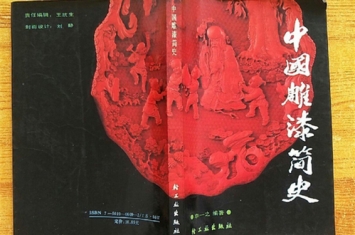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2703号